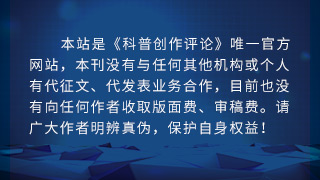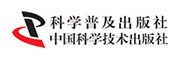失落的知识与“失语”的人群——从《植物与帝国》看多重因素影响下的知识传播
科普创作
吴燕
2021-11-02 09:26
[摘要] 女性主义科学史家隆达·施宾格(Londa Schiebinger)在《植物与帝国:大西洋世界的殖民地与生物勘探》(Plants and Empire:colonial bioprospecting in the atlantic world)一书中,以金凤花为例,描绘了18世纪欧洲人的异域植物知识采集与知识的流传,进而揭示了看似纯智力活动的知识生产是如何被其所处的特定时间与空间中的权力关系所塑造的。同时,作者对卡尔·冯·林奈(CarlvonLinné)的植物命名法的分析显示,由于知识所处的权力关系之影响,一种看似中性的科学语言之所以被接受往往并非因知识本身的胜利,而更像是一种叙事的胜利。作者在此书中体现出的回归历史情境的科学史书写以及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超越,对目前的科学写作具有借鉴意义。
某种知识会被接受只是因为其正确吗?或者换句话来说,某种知识被拒斥以致其传播链条“无疾而终”只是因为其不正确吗?这样的问题乍看起来似乎很容易回答,但近年来的历史研究已不断向我们表明,事情其实并不那么简单。美国历史学者隆达·施宾格的《植物与帝国:大西洋世界的殖民地与生物勘探》(以下简称《植物与帝国》)[1]一书所呈现的就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个案研究。
在2008年出版的《无知学》(Agnotology)一书中,该书主编、科学史学者罗伯特·N.普罗克特(Robert N.Proctor)开篇即写道:“我们生活在一个无知的年代,理解何以至此以及其原因所在极为重要。”[2]vii该著来自2003年和2005年普罗克特与施宾格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加州大学共同举办的两次有关无知学的研究工作坊。与我们通常所认为的无知不同,普罗克特认为,无知有很多不同类型,我们也可以很多方式去思考无知,其中一种无知“像知识一样,具有政治地理学意味”[2]6。《植物与帝国》的研究兴趣就在于此。在《无知学》一书的第二部分“失落的知识,失落的世界”所收入的三个个案研究中,施宾格的这项研究也被列入其中。而在《植物与帝国》一书中,她对这一主题做出了更为详尽的分析与呈现。
该书研究的是18世纪欧洲人在加勒比地区西印度群岛的博物学采集活动,尤其以一种名叫金凤花(Caesalpinia/Poinciana pulcherrima)①的植物为例描绘了彼时异域植物知识的采集、流传甚至消失,并对这些异域知识采集及其接受过程中所体现出的权力关系做出追溯和反思,从而揭示了乍看起来似乎是纯智力活动的知识生产是如何被其所处的特定时间与空间中的权力关系所塑造的。值得一提的是,此书作者施宾格是一位女性主义科学史家,而她在书中尤其关注的主角玛丽亚·西比拉·梅里安(Maria Sibylla Merian)也是一位女性博物学家。性别研究的维度使得施宾格在考察上述权力关系时,对那些一度被遮蔽或隐去的人群与历史有更多观照与洞察,也促使读者在阅读此书时更多一重思考。
一、背景:伴随欧洲拓殖进程的植物知识采集
正如该书副标题“大西洋世界的殖民地生物勘探”所显示的,《植物与帝国》一书所讲述的是欧洲人于18世纪在加勒比地区西印度群岛的博物学采集活动。
欧洲人的异域博物学采集事实上早在亚里士多德时代已经存在。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收集了地中海地区彼时所有关于动植物的描述,而其中所描述的许多动植物是其学生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从遥远的异域寄给他的[3]。早期的异域博物学采集在很大程度上受限于技术条件,但以1492年为标志的航海时代改变了异域博物学采集活动的样貌。历史学者詹姆斯·E.麦克莱伦三世(James E.McClellan III)在其著作《殖民主义与科学:旧王朝时代的圣多曼格》(Colonialism and Science:Saint Domingue and the Old Regime)一书的导言中即写道:“1492年之后的现代科学兴起与欧洲殖民扩张构成了现代世界历史的重要且独有的两个特征。自16和17世纪科学革命以来,科学就以多种方式变得对人类越来越重要……与科学在文化意义上的进步并行的是,在自哥伦布直到19世纪和20世纪的大殖民帝国时期,西方的全球扩张已成为一种重要的历史演变的力量,彻底改变了世界的社会、政治以及经济特征。”[4]1
在同一部作品中,麦克莱伦三世以法国人在加勒比地区建立的殖民地圣多明戈为例,分析了欧洲的殖民进程与科学发展之间的关系,从中也可以看到,二者之间的关联首先就是通过欧洲在圣多明戈的博物学采集活动而得到体现的,其内容包括植物标本的采集、对草药知识的认识以及地方性疾病的研究、当地气象信息的收集等。
麦克莱伦三世的著作以个案研究的方式表明,欧洲人的异域博物学采集与欧洲的全球扩张之间的关联,而在这一大背景之下,殖民地科学虽然的确意在促进殖民地的发展,扩大其经济基础与产出,但其最终指向,或者如麦氏在书中所写:“政府殖民政策的潜在逻辑更在于重商主义与利己主义:加强法国和王室政体——而非(尤其非)圣多明戈——的政治与经济力量。此前对法国殖民地贸易的研究显示,是重商主义的原则和实践,而非资本主义或工业扩张控制着政府对其美洲拓殖的构想。”[4]289-290
自20世纪以来,有关殖民地科学的研究不断得到推进。早在1967年,美国历史学者乔治·巴萨拉(George Basalla)以《西方科学的扩张》(The Spread of Western Science)一文提出现代科学被引入非欧洲国家的三阶段模型,即欧洲博物学家赴新大陆进行博物学调查和采集—殖民地科学—独立科学传统的建立[5]。巴萨拉的三阶段模型为研究欧洲人异域科学考察活动提供了参照,上述提到的麦克莱伦三世的著作亦引用巴萨拉的模式,认为“圣多明戈的科学叙事在很大程度上与巴萨拉的模型相符”[4]296。
巴萨拉的模型所勾勒出的其实是欧洲近代科学实现其在地域上的扩张的线索,它表现为伴随着欧洲拓殖进程展开的欧洲人异域科学考察以及在此过程中西方科学在殖民地的落地,此前有关殖民地科学的研究多集中于此,麦克莱伦三世关于法国圣多明戈殖民地的个案即如此。
同样聚焦于欧洲人在加勒比地区的殖民地科学实践,隆达·施宾格的研究则颇有另辟蹊径之意。与此前的大多数研究不同,《植物与帝国》所关注的不仅是欧洲人在加勒比地区的植物及其相关知识的采集,更对知识从加勒比地区到欧洲的传播做出完整的描绘,尤其对传播链的下游即知识在被带到欧洲本土时的境遇做出深入考察;她以一种名叫金凤花的植物为主要线索,运用史料层层解析,从而揭示出有关金凤花的知识从获得到传播到最终在传播链上消失的历史。
二、知识(或无知)的政治地理学
《植物与帝国》开始于18世纪德国的女性博物学家梅里安的《苏里南昆虫变态图谱》(Metamorphosis Insectorum Surinamensium,以下简称《图谱》)。尽管梅里安首先是一位艺术家,并且是当时少有的远赴异域进行博物学考察并以这部手绘《图谱》闻名的女性博物学家,但这并不是她在《图谱》中所做的全部。她还将从印第安人那里听到的有关植物的见闻也记录在她的书里——比如金凤花被当地黑奴用于堕胎,以免让自己的子女也像自己一样沦为奴隶——这使她成为第一个报告金凤花的堕胎功能的欧洲人。不过在18世纪,在很多欧洲人赴加勒比地区进行植物考察的背景下,获知相同知识的博物学家并不少,书中即写到当时有不少博物学家各自独立发现金凤花在西印度群岛被广泛用作堕胎药,并且把相关的知识记录了下来。但这个知识并没有因为上述欧洲人的发现而被传到欧洲。
金凤花相关知识在18世纪从加勒比到欧洲的传播链上消失,在欧洲异域知识采集的大背景之下,就成为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因为正如隆达·施宾格以及此前的研究已经表明的,18世纪乃至更早时,欧洲人的异域博物学采集固然仍有个人兴趣的成分,但随着重商主义的兴起,已经有越来越多科学考察之外的意义附载其上。“植物学在这个时期是大科学也是大买卖,是向资源丰富的东、西印度群岛输入军事力量的重要因素”,而当时的欧洲政治经济学家则普遍抱持一种理念,即“精确的自然知识是国家财富积累的关键所在”[1]7。
通过这些博物学家的异域采集,不但可以给欧洲带回可能驯化的经济作物或药用植物,还可以丰富其医药知识,而探险家个人更可以从中谋利,可谓一举多得。同时,从当时的社会背景与社会期待来说,这些知识的采集者们也有义务将其所获得的知识服务于公众福祉。有事实为证:曾任皇家学会主席的英国医生汉斯·斯隆(Hans Sloane)于1745年在一封信中解释他为何对一个有效的药方保密多年,从致歉行为本身也可以看到,“到18世纪中叶,对医生而言,考虑公众福祉已渐渐变得比保守医疗秘密更重要了”[1]116。因此,无论从经济角度,还是公众福祉角度,一种草药知识的最终消失就都变成了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
一个有关堕胎的知识的传播,连接起18世纪的欧洲及其西印度群岛殖民地,隆达·施宾格以此为线索进行了深入探究,从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知识传播的历史叙事。
知识的形成发生在传播链的一端,即西印度群岛的奴隶妇女。在殖民地的种植园,生育与拒绝生育显然已不再只是自然人口的增长问题。正如书中援引历史学者芭芭拉·布什(BarbaraBush)的评论所说,“在种植园经济中,种植园主要求‘黑人’生育就如同希望牛马产仔,拒绝繁育变成了一种政治行为”[1]157;奴隶的生育无异于扩大种植园劳动力资源的一种潜在方式,但在奴隶妇女看来,堕胎显然是让自己的孩子摆脱被奴役命运的最直接途径。在这个个案中,草药知识的形成与其原始情境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梅里安在其考察形成的著作中敏锐地觉察到这一点,这也就使得她的考察文本迥异于当时其他的欧洲博物学家的考察报告。施宾格对梅里安、斯隆等人有关金凤花功能的描述进行了对比分析,但她并未执着于对作为个体的男女科学家做出区分或描述,作为一名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者,她更希望探究的问题是,18世纪的欧洲及其殖民地的生育政治如何影响了知识的生产与传播。如果说知识的形成来自殖民地奴隶对其处境的反抗,那么无论从何种角度看来处境都显然好于殖民地的欧洲女性为何最终却与这种潜在的救命药物擦肩而过呢?
作为这条知识传播链的末端,欧洲本土的情况看来比殖民地更为复杂。首先,彼时欧洲占主流话语的重商主义本质上是多生育主义,无论是实现国家财富的扩大、实现经济增长,还是维持常备军队的规模,都需要以人口的增长为前提,在这种背景下,“女性的身体被当成一项国家财富”,而控制生育,包括开发堕胎药等举动都无异于损害国家利益。
其次,医生的角色以及医生为维护自身利益而对话语权的争夺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一方面,重商主义政府寻求医生的帮助,以借助他们的经验和医术来增加人口,比如进行公共卫生预防以及控制堕胎药物的使用;另一方面,医生为了加强自己在医疗上的权威垄断地位,早在前一个世纪甚至更早便与民间医生、药婆、助产士等人群之间存在话语权之争,后者是妇女主要求助对象,也是堕胎草药的主要使用者,而医生则主张任何堕胎药物都是危险的——虽然他们实际上可能并未真的进行过药物试验,并且虽然医生们知道各种方法但因反堕胎立场而对堕胎相关知识闭口不谈,因此只有在孕妇遭遇意外流产等危险处境时,他们才会使用手或外科器械来解决问题,而不是在此之前使用堕胎药物。
最后还有因为宗教和文化的原因而对堕胎行为所抱持的态度。在18世纪的欧洲,随着堕胎被污名化,堕胎药也被视为危险药物。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地理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虽然对害怕生育的年轻女性抱持同情态度,但他在发现美洲印第安人用的堕胎药物很安全,并且认为欧洲对这种药物有需求之时,也拒绝将它们传到欧洲,原因是他担心这些堕胎行为会“恶化城镇里已经堕落的生活方式”[1]279。
至此我们会发现,在18世纪的欧洲,关于堕胎的知识无疑处于各方利益与权力交织的背景之下。无论是在上述何种利益或权力关系中,女性的利益显然都会被排在最后考虑,女性的身体或者“被当成一项国家财富”,或者是医生意欲从助产士手中争夺话语权的筹码,但唯独不属于她们自己。尽管作者多次提醒说,关于堕胎药的知识在当时极少被明文禁止,但当处在上述复杂背景之中,这种知识就成为一个禁忌话题。因此,当金凤花盛开在欧洲各地甚至还被用作退烧药之时,它能用于堕胎的知识却在传播链上消失了。除了金凤花之外,欧洲人在西印度群岛的植物探索中发现了十余种已知的堕胎药,还就地在西印度群岛进行过药物试验,但欧洲医生从未在他们的行医实践中将这些草药当作堕胎药物来使用,也从未将之写入官方报告。
人文地理学者利文斯通在其著作中认为,科学具有地理性,作为一项人的事业,科学处于时间与空间中;而知识的生产、移动以及接受都被其所处的特定的区域,尤其是政治力量和社会地理所塑造,带有当地环境的印记[6]4-15。施宾格以金凤花为中心对殖民地和欧洲本土的考察也正为此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样本,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植物与帝国》可以理解为一部知识(或无知)的政治地理学著作,它讨论的是由“文化和政治抗衡”所造成的无知,而只有将之置于其所处的时间与空间才能凸显其意义。
三、“失语”的人群:被“偷窃”的历史
除了寻找失落在传播链上的知识及其原因,在《植物与帝国》中,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超越也让那些一度被遮蔽的人群重新回归他们在历史中的位置。
当作者发问“是欧洲人经过科学训练的双眼才让他们发现新药的吗?”时,答案其实已经揭晓。她提醒我们,在关注欧洲博物学家——无论是“珍奇柜博物学家”②,还是旅行博物学家——的同时,也不能忽略其他旅行者及其对西印度群岛植物知识的贡献,比如非洲奴隶以及美洲印第安博物家,正是在他们的帮助下,尤其是因为他们所提供的信息,欧洲博物学家才找到了后来那些著名的热带药物[1]31-92。笔者也由此想到,与《植物与帝国》中的个案相似,美国历史学者范发迪(Fa-ti Fan)几年前在其著作《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British Naturalists in Qing China:Science,Empire and Cultural Encounter)中也对当时参与到英国人的博物学采集活动中的中国人给予了关注,这些当地人的身份各异,从官员到草药商到画师不一而足,与这些当地人的接触与交流是当时英国博物学家在华博物学考察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7]。
不只是在殖民地,在欧洲本土的知识采集活动中也同样如此。例如18世纪欧洲的采药妇女乃至成功的女性医者往往也是医生们收集治疗方法以及药方的信息源,书中尤其提到一位来自英国的史蒂芬斯夫人,她不仅精通医药知识,而且还能制备药方,特别是一个可以治疗结石的药方,其疗效得到验证之后,史蒂芬斯夫人便获得了一笔奖金,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政府出资买下了她的药方。在法国也有类似的例子。但是正像作者在书中所写,“就算治疗方法最后被采纳并收录在欧洲各种药典中,掌握这些方法的女性大部分并没留下名字,就同西印度群岛上提供药方的大部分本地人和奴隶一样”[1]119。
作为旁证,作者以种痘术在欧洲的应用为例,细致讨论了这些无名者如何在历史书写中被“忽视”,进而被“遗忘”的方式。因为在家庭中的角色,女性在将种痘术引入欧洲的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所有关于发现种痘术的叙事都更强调是“有学识的欧洲人将知识从君士坦丁堡传到欧洲”,除了最著名的蒙塔古夫人之外,更多女性在这种叙事中都被简化为类似“摩里亚半岛的希腊妇女”之类的符号。而彼时的英格兰和新英格兰的很多医生都拒绝承认妇女在种痘术上的作用,或者对之加以贬低,或者认为如此重要的手术只有“医术高明的内外科医生”才能操作和掌控。
在英雄凯旋式的科学史书写中,上述人群往往是被遮蔽的“失语”的人群;而通过植物的命名法,这种遮蔽进而得到制度上的巩固。这正是作者在此书第五章“语言帝国主义”中所要分析的内容。自然王国的无序的确需要以某种命名来赋予其某种秩序,而一个作为统一标准的命名法无疑会带来这一秩序,林奈的双名法意义正在于此。但是依然地,事情其实并不那么简单。
林奈在选择用什么人物来命名植物上有他自己的一套想法。这个名录中的人物以欧洲男性植物学家或者他所认为的精英人物为主,比如金凤花在林奈体系中被命名为Poinciana pulcherrima,就是为了纪念一位名叫菲利普·德·庞西(Philippe de Lonvilliers de Poincy)的17世纪法国殖民地总督[1]229。但以《图谱》闻名的梅里安以及其他女性植物学家或发现者则未被包含其中,即使她们在植物考察或研究方面颇有声望。不过并非所有女性都不在林奈的考虑之内,比如有几位出身名门的女性就被林奈选中用以命名植物。此外,尽管有大量的植物学名从当地的美洲印第安语言衍变而来,尽管印第安人在欧洲人的植物发现与采集活动中起到重要作用,但除了一位名叫格拉曼·戈塞(GramanQuassi)的苏里南人之外,再无其他当地人被用以命名植物,而戈塞作为一名被释放的奴隶,其经历颇有传奇色彩。[1]247-254
通过他的命名法,林奈一方面确立了欧洲在植物学史叙事中的核心地位,另一方面也确立了一个他所认为的植物学发现史中的(欧洲)精英名录——他用这些精英们的名字来命名某个属,通过这种方式,实际上也就相当于完成了一个林奈眼中的植物“发现”史叙事。而在这样一个植物学及其历史书写中,一旦某种异域植物被纳入这一命名法,也就相当于从其本土的文化语境中被剥离出来,并置于欧洲人所接受的知识框架里,成为欧洲人植物“发现”史的一部分。
英国历史学者杰克·古迪(Jack Goody)在其著作《偷窃历史》(The Theft of History)中写道:“书名中的‘偷窃历史’意指历史之由西方掠取。就是说,根据在欧洲(通常是西欧)的地方尺度上发生的事,历史被概念化并加以呈现,然后强加给世界的其他地方。”[8]这也就意味着以一种欧洲中心的历史叙事呈现世界史,以此观照,林奈足不出户而为植物世界规定的秩序标准,其实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成为欧洲中心的植物学史叙事的基本概念化框架。施宾格在书中也提醒我们说,林奈的分类法与命名体系并非没有竞争者,其最终胜出“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确立和传播时的种种偶然性”,只是当它一旦被接受成为一种标准,人们便很容易遗忘这一偶然性以及历史上曾有过的其他可能性;更进一步地,人们更可能将这种偶然性的胜利视为必然,并心安理得地以之作为唯一合理的选择和知识本身的胜利,而事实上它更像是一种叙事的胜利。因此,作者以林奈为例对命名法的分析,其意义首先就在于指出“科学语言”并非如它看起来的那样中性,同时将一种“被偷窃的历史”重新放回其本来的地方。
四、余论
即使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植物与帝国》一书首先都是一部学术著作,但因其具有较强的叙事性,且译文流畅,所以对于非学术读者来说也同样易读。事实上,从公众理解科学的意义而言,该书也的确为面向公众解说科学及其历史提供了有益的视野和可供参照的样本。
人文地理学家诺埃尔·卡斯特利(Noel Castree)以“谁定义地理学?为了什么目的?为了谁的利益?”的追问提出了反思地理学在诞生时期的权力关系的必要性[9]。通过隆达·施宾格在《植物与帝国》一书中所做的工作可知,这一追问及反思在植物学史领域同样适用。正如作者已经在书中揭示的,知识的生产、采集到传播及最终被纳入某种知识系统的过程并非只是探索自然的纯智力活动,一种知识体系被广泛接受也并不只是(或并不主要是)知识的胜利,其间充满利益的较量与话语权的争夺。而将科学活动置于其所处的历史情境做出观照是实现上述追问与反思的必要途径。这在目前的科学写作中是较为薄弱之处。
施宾格在书中写到欧洲人带着其固有的理论框架去往异域进行植物采集活动时曾评论说,这些欧洲人只是把“剥离了背景故事”的标本送到了欧洲[1]106。这也使笔者联想到此前看到过的《图谱》的其中一个中译本。像所有博物学绘画图书一样,该书制作精美可人。不过,假如不是因为读了《植物与帝国》,笔者也并不知道梅里安的原书内容比该中译本丰富得多。施宾格在书中提到她之所以会关注金凤花,原因之一就是被梅里安对它的评述所打动,即“梅里安直接将堕胎置于殖民地冲突的语境中,认为奴隶杀死后代是一种政治反抗的方式”[1]129。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图谱》其实并不是一位颇有文艺气质的博物学家的博物绘画集,而具有更深层的文化意蕴,它不仅向我们呈现了苏里南的自然生态,也显示了彼时彼地的殖民地社会生态。但在笔者读到的中译本中,关于金凤花的说明文字就只有一句:“烟草天蛾在孔雀草上,这种被称为‘巴巴多岛之荣’的植物,花朵红里透黄,在法语中的意思是‘小火焰’。”[10]书中其他图画的说明也基本上仅保留了对植物和昆虫的介绍,因此选编该书的主旨看来是要展示西方博物学的成果,呈现那些美好的自然物——假如真是做此考虑,其做法倒多少有点像是施宾格所评论的“剥离了背景故事”的标本展示了。
作者简介:
吴燕,内蒙古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近代中西科学交流史。
参考文献
[1] 隆达·施宾格.植物与帝国:大西洋世界的殖民地生物勘探[M].姜虹,译.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20.
[2] PROCTOR R N,SCHIEBINGER L.Agnotology: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Ignorance[M].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
[3] 罗伯特·赫胥黎.伟大的博物学家[M].王晨,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4] MCCLELLAN III J E.Colonialism and Science:Saint Domingue in the Old Regime[M].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0.
[5] BASALLA G.The Spread of Western Science[J].Science,156(3775),1967:611-622.
[6] 大卫·利文斯通.科学知识的地理[M].孟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7] 范发迪.知识帝国: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M].袁剑,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8] GOODY J.The Theft of History[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
[9] 孙俊.知识地理学:空间与地方间的叙事转型与重构[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
[10] 梅里安.苏里南昆虫变态图谱[M].郑颖,编译.北京:北京出版社,2016.
①本书所提到的“金凤花”为豆科植物,拉丁学名Poinciana pulcherrima,由林奈于1753年命名。在现代植物学著作中,Poinciana pulcherrima已不常用,而习惯用Caesalpinia pulcherrima这个拉丁学名。
②有关“珍奇柜博物学家”的相关解释可参见《植物与帝国》中文版第16页脚注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