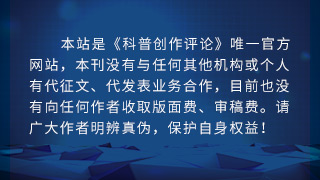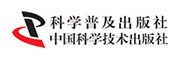推开永生之门:21 世纪英美科幻作品中的三类科学实验
科普创作评论
安帅
2022-10-10 14:05
[摘要] 对于永生的向往是人类的共性,也是文学作品的经典母题。进入21世纪后,高科技为创作进一步提供助力,特别是成为科幻作家想象未来的翅膀。其中,克隆、数字化和低温休眠技术尤其受到青睐,成为虚构世界中科学实验的聚焦对象,扮演着“推开永生之门的钥匙”的重要角色。然而,科技的深度介入带来的是对传统伦理体系的僭越,特别是对人性的挑战。对于生物学、社会学和伦理学等不同层面的人的再思考,成为这一类科幻作品的现实观照。
18世纪初,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在代表作《格列佛游记》(Gulliver’s Travels)中,通过塑造斯特勒尔布勒格这个“变种”(variant),在时值拓荒阶段的英语小说世界中率先推开了神秘的永生之门。不过,在这位讽刺大师笔下,这一族群表面的光鲜很快就被消解,让小说叙述者由艳羡转向鄙夷和恐惧:“当他们活到80岁,也就是这个国度通常认为的寿命极限,他们不仅有其他老年人身上所有的愚蠢和脆弱,而且由不死这个可怕的预期衍生出更多的(丑恶)。”[1]斯威夫特嘲讽的是人类虚妄的永生之梦,证明对于死亡的敬畏之心是人性不可抛除的一部分。个体对“人类”这个共同体的想象,很大程度上依赖死亡——若能有法子不死,则非我族类。
斯威夫特不缺乏文坛后继者。不过,和斯式小说朴素的乌托邦建构不同,现当代作家再次聚焦人类古往今来的永生之梦时,已经为自己的想象力插上了科学的翅膀。特别是,越来越多的当代学者认识到科学与文学并不属于两种文化,而是一种双向的互动[2]。在这样的学科语境下,小说家“一本正经”地尝试科学实验,无疑为文学赋予了新的现实功能,又丰富了科学的内涵,为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两大学科之间建立起一条新的纽带。其中,若聚焦21世纪英美文学中的科学实验叙事,有三类高科技备受瞩目,分别是克隆、数字化和低温休眠。它们在严肃小说家笔下得到表征,同时通过流行文化的方式走进大众视野,不断开拓并挑战着我们对于物种演化和生命本质的认知
一、生命置换:从《别让我走》①到《逃出克隆岛》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的《别让我走》聚焦的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克隆人。但小说叙事的一个不寻常之处在于,在文本内部的故事世界中,尽管叙述者主要采用的是第一人称回顾视角,但她并没有对关键的情节予以“预叙”(prolepsis)②;相反,在其回顾的三段人生中,转为第一人称体验视角的“我”和其他两位主要小说人物起初对自己的特殊身份并不自知,因而经历了曲折的身份探索与发现之旅。相应地,在文本外部,读者也经历了复杂的推理过程——这让该小说可以归入“侦探小说”的类别,因为一直要到小说结尾悬念才会被揭晓,这些人物身上种种的不寻常才会得到解释。小说的第一人称叙述促成了这样的“延迟满足”:读者没有办法跳脱凯西的有限视角以提前揭晓谜底;读者始终需要更多的信息才能对看似平淡无奇、实则蕴含着巨大玄机的小说开篇作出“解码”——主人公的姓氏为什么会是一个字母H?“护工”(carer)与“捐赠者”(donor)隶属什么样的产业,为什么会出自同一所“学校”呢?事实上,直到谜底揭晓,读者才会将这本小说和“科幻”联系起来。正如有批评家指出的那样,“作者用冷静客观的零度叙述摒弃生物克隆小说的一切科幻因素,强化女性克隆人丰富的感性生命,同时将读者置入一种克隆生命的体验之中”[3]。
《别让我走》成书于21世纪初,距离世纪之交人类科学史上一件大事的发生——克隆羊多莉的诞生——不足10年的时间。可以说,以虚构叙事来表征当时的这股“克隆热”,表明作为小说家的石黑一雄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一事件对于学术界之外的重大意义——就像现代人深知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一经出版,引发的不只是生物学或自然科学界的一场认知革命,而是整个维多利亚社会都感受到了“地震波”。
人类生命体的运转和延续的最大挑战来自器官随衰老或病变而来的衰竭。如果说现代生理医学依然无法阻挡衰老的进程,且对某些疾病依然束手无策的话,那么,不如就像维护一台机器一样,索性更换掉出现老化或故障的零件。长期以来,这个策略的掣肘在于人体器官的稀缺性,尤其是一些重要器官对于个体而言的不可再生性。克隆技术的出现在理论上解决了这个难题:既然器官来源于人,那么就“生产”一批人作为“库存”,需要的时候从母体摘取器官即可。这种新的实践,听上去既因为满足人类的共同需求而具有广阔的市场,又有现代科技的进步作为支撑保障。这样,人类的永生之梦再一次被送上了实验台。
石黑一雄在小说中建立了一个以克隆技术为核心、以推开人类的永生之门为己任的国际科学共同体。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看,这次实验关乎人类命运,因而具有重大的研究意义:克隆技术的发明,让实验具备必要的理论支撑,可在前人的基础上走得更远;研究得到多国政府支持,资金充足、配套完善;诸如黑尔舍姆(Hailsham)这样软硬件一流的学校提供了先进的实验设备;跨国资本运作之下,其实验成果一旦投放市场,可精准匹配用户。以科研项目的评估标准而论,这无疑是一次完美的实验设计。
然而,科学共同体“具有区别于一般社会群体的特定规范和气质”,除追寻科技进步外,“应当承担的很重要的社会责任是倡导并践行负责任的科学行为,如科学伦理问题”[4]。批评家也指出,需要从两个方面来“评判《别让我走》的科学性”,一是它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小说创作年代的科学高度,二是它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伦理规约[5]。《别让我走》中的这一次科学实验引发的最大伦理争议在于,究竟该不该将包括主人公在内的这个克隆人群体视作“人类”?如果是,那么是否该让他们享有基本的生命权?如果不是,那么他们与人的区别在哪里?
与其说石黑一雄直面科技进步与科学伦理的冲突,毋宁说他拷问的是“人类”这个地球上最大的共同体存在的根基是什么,即人性的真谛为何。正如有批评家指出的那样:“石黑一雄的生命叙事不是平面化、模式化的受害者叙事,也不是常见的以痛苦或苦难为主基调的创伤叙事(尽管小说也有对露西‘捐献’后凄惨而死的描写)。总体上看,这是一种宁静幽远、意味深长的回忆叙事,是一种反抗遗忘的见证叙事。”[6]在石黑一雄标志性的细腻的笔触下,读者见证的是三个富有情感的个体的成长史。读者需要辩证看待他们不同寻常的身份。在谜底揭晓之前,凯西、露丝、汤米三人之间微妙的情感关系以及在不同时期的权力结构,与人类族群的共同体验并无丝毫差异——甚至,舍弃小说的结尾,这部小说可以被轻易地改写成一部校园情感小说。正如小说中黑尔舍姆的创始人谈到的这所学校的意义:“最重要的是,我们向全世界表明,如果学生能在人道、文明的环境下长大,他们就有可能变得情感细腻、智力出众,不输给任何一个普通人。”[7]另一方面,正因为考虑到他们的特殊身份、考虑到始终有一柄利剑悬在他们头顶上方,才会愈发让人体会到这段友情、爱情、手足情的弥足珍贵——尤其是当他们发现了自己的“非人”身份之后,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依然守卫着彼此间真挚的感情。
克隆题材影片的发展已有半个世纪的历史,其早期代表作品是《扎卡里·惠勒的复活》(The Resurrection of Zachary Wheeler)和《来自巴西的男孩》(The Boys from Brazil);不过,此类影片真正引发全民关注,可能离不开阿诺·施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的《第六日》(The 6th Day)的影响。此外,《别让我走》出版的当年,美国梦工场(Dream Works Pictures)出品了一部重量级的科幻电影——《逃出克隆岛》(The Island)。和石黑一雄的情节设定一样,这部电影中虚构了一个神秘的科学组织,批量生产克隆人;当这些克隆人被选中前往梦想中的神秘岛的时候,实际上就是“收割”他们的器官、移植给他们的“原型”之时。除了科学创意上的趋同,两部作品更重要的相通之处在于将情感视为定义人性的根基。电影的男女主角在对自己的特殊身份尚不自知的时候即萌发出懵懂的爱情,而在一起出逃到陌生的大世界后更是经历了感情的不断升华。无论是小说作者,还是电影导演,都用这样的叙事方式让读者对克隆人产生情感上的认同,消解人与非人/工具人之间的界限。人类通往永生之门在现代科技的作用下被短暂推开,但在迎面而来的一阵血雨腥风后悄然关上
二、云端数据:从《奇点遗民》到《黑镜》
《奇点遗民》(Staying Behind)是当代科幻新锐作家刘宇昆(Ken Liu)2011年发表的一部短篇小说——后来,作者于2017年出版了同名的短篇小说集,将这个故事列在“未来三部曲”居中的位置。《奇点遗民》同样采用的是第一人称的有限视角,不过相较于《别让我走》这样的长篇小说,其在叙事时间和空间方面都更加紧凑。主人公“出生在奇点元年,也就是第一个人被上载到机器的那年”[8]67,之后,大多数人选择以数字化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如果说前面两部作品中的科学共同体都以攻克人类的生理学弱点(衰老、疾病)为己任,那么,刘宇昆笔下的“永生公司”则要走得更远:“老人和病入膏肓的人率先进行了数字化,当时的费用还很昂贵。后来随着费用的降低,越来越多的人为之排队等候。”[8]68主人公拒绝这样的数字化永生,将他们称为“活死人”,成为依然以实体形式存在的少数者。
需要注意的是,小说中这个“奇点时代”的兴起,并非源自科技的突飞猛进。其实,刘宇昆和石黑一雄一样,都算不上“硬核”的科幻作家。在这个故事中,生命完成数字化到底需要哪些具体的步骤、架构于什么样的科学机制之上,作者并没有明确阐释。这样的叙事留白其实在故事层面上有着重要的意义,一个重要的含混(ambiguity)由此而来:人类的科技到底有没有达到这样的高度?数字化是确有其事,还是一场商业骗局?我们需要对两种可能都予以思考。
若数字化为真,那么,我们需要对这些“永生人”进行一次全方位的种属界定。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脱离了肉体,是否还能称之为“人”?即对于人类这个共同体的想象,有多大程度上依赖于肉体,或者说依赖于有时间限制的存在?小说中,最初抵制数字化的母亲谈到“我真正活过,也要死得真实。我才不要变成数据记录,这世上有比死亡更惨的事”,并教导子女“正是不可避免的死亡造就了人类”[8]72。这里,作者借人物之口对“永生”重新定义:“我们死亡是给后代腾地方,每个人在后代身上延续,这才是真正唯一的永垂不朽。”[8]72这样的观点,实则是将生命的归属/主体由个人上升到集体,或者说上升到作为一个物种存在的人类。这或许解释了为什么古往今来对于永生的探索终究都是大梦一场:永生从来不属于个体。基于此,经历数字化的人需要一个新的身份,要么,可以将其视为“智人种”的一个变种,是脱离了实体存在的“智人”;要么,不只难以将其继续视为“智人”,恐怕现有的“界门纲目科种属”体系都无法安放,只能将其视为与生物平行的某种“存在”(being)了。如果主体已经不再被定义为人类,那么他们的存在状态则无法代表人类理想中的永生。和克隆技术一样,这样的“数据人”也将触及伦理的红线。正如有批评家指出的那样,“科技研发必须坚守人类中心的信念,永生公司的数码技术正像生物技术一样,会让人类丧失人性,而正是人性支撑我们成为我们,决定我们未来的走向”[9]。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这里的“人性”更多还是传统人文视角下的人性。
但我们不得不面对另外一种可能,也是读者和研究者不情愿面对的一种可能:若数字化技术为假,那么这实则是披着科技外衣的一场屠杀,并且非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惨绝人寰的种族灭绝运动可比,因为这一次的对象是全人类——“每个上载到机器的人都会抛下一具没有生命的躯体,毁坏性的扫描过程把大脑弄得血肉模糊”[8]67。这样,这篇小说恐怕要由“科幻”转向“恐怖/悬疑”小说的类别。此外,永生的“超现实”之所以成为时代主题,归根结底在于地球上的“现实”正在丧失从前的吸引力:“世界正在陷入一片混乱,战争的威胁和真实演绎遍布各地,大家你争我夺、杀个不停。”[8]68如此,刘宇昆在小说中的关切点依然在于“现在”,并不一定要将其划入“未来”系列。这实则是作者借用科幻题材对社会现实的一次深度预警。在这种可能性下,永生不过是又一场消费主义的狂欢;盛宴过后,恐怕不只是杯盘狼藉,更是满地白骨无人收。现在看来,刘宇昆对于战争的预警并不为过,我们确实需要看到“战争与和平”问题正在嵌入到新的时代主题中。当然,作者预警的还有科技深度介入之后的人类生活。正如有批评家看到的那样,“作为文化思潮的赛博格是对20世纪晚期科技发展状况的回应,即当身体与非身体、人与非人、有机体与非有机体(机器)的界限变得含混可疑,人类已然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复杂样态”[10]。
总结而言,无论是哪种可能,人类的永生之梦将再次化为乌有。更重要的是,若执念过盛,则会适得其反,换来的是死亡的加速,而这既包括个体的消亡,也包括群体性的灭绝。
人脑数据化、意识上传在近些年的影视作品中同样成为热门话题,如2020年以来已播出两季(共17集)的美剧《上传》(Upload)正是对这项技术革新如何颠覆生命的存在状态的最新想象。《奇点遗民》发表的同年,日后成为英国科幻影视里程碑的《黑镜》(Black Mirror)系列在第四频道(Channel4)开播,其中,第二季的第一集《即刻归位》(Be Right Back)聚焦的也是数字化人类。在这个故事中,女主人公作为测试者体验了一个新型应用程序:通过整合人在网络上留下的痕迹(如各类社交网站的发言、聊天记录、邮件等),她刚刚死于车祸的男友以人工智能的方式“起死回生”,可以与她通过文字、语音进行云端互动,并且最终以仿生机器人的“高级”形式来到她的生活当中。与《奇点遗民》相比,这个故事既有从人到“算法”的正向数码化,又有从“算法”(虚体)到“人”(实体)的逆向操作。在刘宇昆的笔下,无论我们相信哪一种可能性,人类都无法实现永生——要么是非人类的胜利,要么是人类的灭绝;《黑镜》则让我们再次直观地看到了人类挑战自然规律之后落入的虚无。让阿什的生命真正得以延续的,是他的遗腹子;仿生人不过“虚有其表”,纵使是“深度学习”之后也无法习得人类正常而复杂的情感反应,因此无法带来原有秩序的回归。这就是为什么主人公最后让这个回归后的男友跳下悬崖,再次经历“死亡”。仿生人最后被锁在阁楼上,成为了科幻版本的“阁楼上的疯女人”③
三、低温休眠:从《绝对零度》④到《氧气危机》
唐·德里罗(Don DeLillo)是当代美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著名文学评论家、耶鲁大学教授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视德里罗为美国当代四大小说家之一[11],而且近些年他一直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几大热门候选人之一。在半个多世纪的创作生涯中,科技始终是德里罗关注的一个重要话题。他被学界视作诠释“文学与科学互动关系”的代表性美国作家,并且是为数不多真正“懂行”的当代小说家[12]。在他截至2022年7月公开发表的19部小说中,有3部可以被划入“科幻小说”的门类——早期小说《拉特纳之星》(Ratner’s Star)外加最新的《绝对零度》(Zero K)和《死寂》(The Silence)。其中,《绝对零度》关注的是人体低温保存/休眠(cryogenics)这一项技术。
《奇点遗民》中的“我”拒绝承认那些向自己发出召唤的文字具有可以等同于自己亲人的主体,《绝对零度》中的“我”也是如此——在杰弗里看来,眼前陈列在玻璃舱中的只是“一具女性的尸体/身体”[13](英文中的body有身体和尸体两种含义,在这个语境下是含混的)并不是自己的亲人。这也将他与“荟萃”(Convergence)这个科学共同体中那些高科技的虔诚信徒们区别开来,让他成为又一个固执地坚守传统存在方式的“奇点遗民”。可以说,德里罗和刘宇昆用相似的方式拷问人性的真谛。此外,人体低温技术和人体数码化最初都是为了应对在当下无解的疾病,但奇点时代的大众不加区别地纷纷走向了“云端”,而在德里罗的这个故事中,如果说身患绝症的母亲的休眠尚且没有背离科学伦理,那么,她健康无恙的丈夫选择随她而去,主动走进了低温舱、走向了生与死的中间地带,陷入了灵薄狱⑤(limbo)一样的状态,则是对人类现有伦理体系的十足挑战。
从文化传统来看,“殉情”这种特殊的自杀方式并没有成为禁忌,东西方皆是如此,是因为其依然符合“爱情”这一人类共同体基石的规约。这只是一种极端的情感表达,并没有触碰到伦理的红线。然而,这个故事的特殊性在于,妻子阿提斯并没有“死”,相反,从理论上讲,她的生命将在未来重启,是走向了“永生”。这就是说,丈夫罗斯选择的也是一条永生的通道。殉情在伦理上的合理性在于以个体生命的终结换得情感的永生,既然罗斯并没有经过“赴死”这个终极考验,那么便无法再享有这样的伦理豁免权。此外,殉情在伦理上之所以能够成立,甚至被镀上一定浪漫主义色彩的重要原因,在于死亡带来的未知。死亡开启的是另一段旅程,是活人无从想象的。这样的未知包含多种可能,灵魂的重聚为其中一种——在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的名诗《乌鸦》(The Raven)中,刚刚失去爱人的叙述者就向通灵的乌鸦发问,是否在另一个场域见过她——不过,从理论上来说,罗斯和阿提斯面临的是可期的未来,他们的生命体征被暂时冻结,但终究会有重启的一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是一次改良版的殉情,或者说消除了悲情色彩的殉情。但德里罗的关注点并不在未来,而在当下——纵使主人公的父母能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点重新携手与共,也无法抹除当下低温舱中这一段可长可短的“活死人”时光。传统殉情模式中,身体的死亡是可能的灵魂自由的起点,然而,在这个高科技介入之后的案例中,二人的“灵”与“肉”同时被禁锢在了密闭空间之中。低温舱的一进一出之间,有可能是无限的时间、无止境的虚无。如此,便失去了殉情的意义:低温舱中是两个独立的个体,无法以肉体或精神的方式建立起联系。
进入玻璃舱中休眠的阿提斯,不禁让人想到德里罗的代表作《地下世界》(Underworld)中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在小说的“尾声”部分,主人公尼克在考察完位于哈萨克斯坦塞米巴拉金斯克的地下核试验基地之后,参观了当地一个医疗研究所——其更形象的名字是“异形博物馆”(The Museum of Misshapens)。这里陈列着各种各样的畸形人,“有的有两个脑袋,有的脑袋有两个身子那么大,有的是一个正常脑袋长在了错误的地方——嵌在右肩上”,还有的是所有的器官的位置都发生了错置[14]。他们祖祖辈辈都生活在位于核试验基地下风向的村落中。核污染之下的环境对于局外人而言是超现实的存在,对于当地人而言却是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小说因此将对核战争、核武器竞赛的批判推向了顶峰。《绝对零度》中,高科技的临床试验取代核试验成为阿提斯非人化的罪魁祸首。这里的反讽之处在于,人体低温技术需要的温度并未达到绝对零度,甚至还相去甚远——从技术上来讲,人体低温需要的温度为-196oC,而绝对零度为-273.15oC。但这样的尝试意味着人类的绝对零度时刻:人性在这里被冻结,人类主体要么暂时隐退,要么已经消亡。
低温休眠的概念在20世纪60年代得到普及,自此之后在科幻作品中屡见不鲜,大名鼎鼎的《星际旅行2:可汗怒吼》(Star Trek II:The Wrath of Khan)和《美国队长:复仇者先锋》(Captain America:The First Avenger)都在此列。进入21世纪20年代,美国奈飞公司(Netflix)推出了科幻电影《氧气危机》(Oxygen),再次将焦点对准这项充满争议的技术。这部电影首先可以被视作《绝对零度》的续篇,因为其情节以女主人公从发生故障的低温舱中苏醒过来为开端。德里罗并没有探讨如果因为遭遇意外事件导致人提前苏醒过来会有什么后果,而这部电影正是对此的想象:人可能会只有“前世”记忆的残片,陷入身份的真空,同时可能面临舱内氧气衰竭而又无法逃脱的绝境。不过,在观影完毕之后,我们会发现剧中还涉及克隆和意识数字化这两项技术——低温舱中的女主人公伊丽莎白其实是克隆人,她之所以进入深度睡眠,是因为地球遭遇致命病毒的攻击,真正的伊丽莎白将自己的记忆数据化并复制给了克隆人,而后将其送上了宇宙飞船,为的是在遥远的外太空为人类保留星星之火。如此,《氧气危机》是一次更加宏大的科学实验,合三种高科技手段之力向永生发出了终极挑战。电影结尾,克隆人最终得以在新的星球上延续生命。只不过,这到底该被视为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永生,还是一个新的变种的新纪元,恐怕还有诸多探讨的空间
四、结语
本文探讨的三位作家中,石黑一雄和德里罗并非专职的科幻作家,而刘宇昆在翻译领域同样成就斐然。与其说“科幻”创作是他们的目的,毋宁说是他们借用的“外衣”,以这种特别的文体来表征当代社会的不同面向,以虚构文学的方式书写当代历史。三位作家都选择了“让未来在现在发生”的叙事策略,将焦点对准人性本身。其实,科幻文学史上那些赫赫有名的大师,同样可能在作品中倾注了鲜明的“现实主义”观照。比如,威尔斯(H.G.Wells)在《时间机器》(The Time Machine)中探讨人性善恶的两极分化,在《隐形人》(The Invisible Man)中想象剥离了社会属性之后人类的困境。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则更加大胆地在《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建构了一个人类从生到死的每一阶段都有科技深度介入的未来社会——在这个新世界中,人类更加看重的是肉体的“不老”而非“不死”,以生命的长度为代价换取了特定阶段的广度,免除了衰老和疾病的侵扰。与这些深受达尔文的进化论影响的前辈一样,当代作家同样试图动用作家的特权给出生命演化的“诗性真相”——特别是,与赫胥黎相较,他们试图证明“长生”和“不老”都会颠覆“人类”的定义。本文中探讨的作品,从小说到电影文本,莫不是用问号直击人性:以克隆、数字化、低温休眠为代表的高科技究竟对人类意味着什么,带来的是物种的永生通道,还是一如往昔面对未知的恐惧?这些作品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毋庸置疑的是,“人”这个概念正在科技环境中不断“异延”。
通信作者:安帅,中国科学院大学外语系讲师,研究方向为叙事学、科学与文学。
参考文献
[1] SWIFT J.Gulliver’s Travel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2] MEYER S.Introduction[M]//MEYER S.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Literature and Science.Cambridge: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8.
[3] 支运波.冲突与弥合的寓言:论《别让我走》的生命政治与生命价值[J].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1(3):112-119.
[4] 周忠和.科学进步与科学共同体的社会责任[J].科技导报,2019(2):36-39.
[5] GRIFFIN G.Science and the Cultural Imaginary:the Case of Kazuo Ishiguro’s Never Let Me Go[J].Textual Practice,2009(4):645-663.
[6] 张和龙,钱瑜.权力压迫与“叙事”的反抗——《别让我走》的生命政治学解读[J].当代外国文学,2018(4):102-109.
[7] ISHIGURO K.Never Let Me Go[M].London:Faber and Faber,2005.
[8] 刘宇昆.奇点遗民[M].耿辉,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
[9] 肖画.后人类视阈中的人性反思——刘宇昆科幻小说论[J].文学研究,2018(2):12-34.
[10] 王雨童.尚未陨落的未来:浅谈刘宇昆的科幻叙事伦理[J].文艺论坛,2019(5):73-79.
[11] BLOOM H.Introduction[M]//BLOOM H.Bloom’s Modern Critical Views:Don DeLillo.Broomall:Chelsea House Publishers,2003.
[12] SCHOLNICK R J.Permeable Boundaries:Literature and Science in America[M]//SCHOLNICK R J.American Literature and Science.Lexington:TheUniversityPressofKentucky,2010.
[13] DELILLO D.Zero K[M].New York:Scribner,2016.
[14] DELILLO D.Underworld[M].New York:Scribner,2003.
①《别让我走》(Never Let Me Go)为2011年由朱去疾翻译,译林出版社出版的译本;2018年,由张坤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译本名为《莫失莫忘》。本文使用2011年译本的译名,特此说明。
②法国叙事学家热奈特(Gerard Genette)在《叙述话语》(Narrative Discourse)中区别了故事(story)和话语(discourse)在时间顺序上两类主要的断裂现象:预叙(prolepsis)和倒叙(analepsis)。简单来说,预叙指的是在话语层面提前透露了本该在后文才会发生的事件。
③《阁楼上的疯女人》(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是当代批评家对于英国文学史上长期受到压制的女性形象和女性作家的重新解读,直接指代的是《简·爱》(Jane Eyre)中主人公罗切斯特的原配妻子、后来的纵火犯伯莎·梅森。
④《绝对零度》(ZeroK)一书中译本已于2020年由译林出版社出版,译者靖振忠,译名为《零K》。本文考虑到整体行文的直白流畅,故通篇采用《绝对零度》一名,特此说明。
⑤灵薄狱,即地域的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