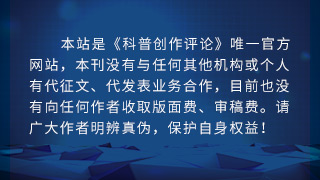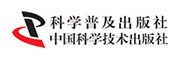论《双百人》中机器人安德鲁“为人”的两种进路
科普创作评论
荆祎澜 刘文霞
2023-01-31 12:54
[摘要] 《双百人》中的安德鲁是一名拥有自由意识的“非理性”机器人,他尝试多种方法使自己成为“人”,可分为两种进路:社会维度进路与技术维度进路。从社会维度看,他追求法律意义上的自由与不被伤害的权利;从技术维度看,他通过研发人造器官将自己改造为有机体,并设法以此延长人类的寿命,来扩大“人”的定义。但这些尝试并没有使他成为“人”,因为他无法消除人类的恐惧。最终,安德鲁使自己大脑的电位缓慢流失直至死亡才使他被认可为“人”,而死亡正是两种进路的交点。
机器人安德鲁是艾萨克·阿西莫夫科幻小说《双百人》(The Bicentennial Man)中的主人公。该作品于1977年获雨果奖,并于1999年被改编为电影《机器管家》(Bicentennial Man),不过,它在受到称赞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些批评,如被认为是空洞的人文主义且没有展现任何智能,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也常被作为哲学、伦理学、神学等严肃的批判性研究的主题[1]。而本文将就安德鲁成为人的诸多尝试以探讨机器人“何以为人”这一问题。
《双百人》讲述了拥有自由意识的机器人安德鲁尝试成为人的故事。这一过程并不顺利,他作为有意识的机器人,为人类所恐惧并被敌视。他在小说中追求了自由与不被伤害的权利,但这都没有使他为人类所认可。他或许可以成为道德主体、法律主体,但就是无法被当作人。安德鲁后来意识到,他无法为人的原因是其不朽的机械躯体。于是安德鲁利用技术手段扩大了人的定义,但最终使他得以为人的却是生命的终止。驱使安德鲁成为人的并不是他理性的需求而是情感上的非理性需求。正如其弥留之际紧随“人”的意识之后的是小小姐一样——他希望与亲近的人变得一样。而他的这种选择,也正是其拥有自由意识的体现。
一、安德鲁的困境与机遇
(一)困境:人类对机器人的恐惧
小说中两次提到人类对机器人的恐惧。一次是安德鲁被两个人类要求脱衣服并肢解自己时,一次是安德鲁提起诉讼要求法院承认机器人权利时。人类的恐惧是安德鲁被区别对待并难以成为人的重要原因。在早期的机器人形象中,机器人总是以奴仆、反叛者、令人恐惑的“它者”形象出现[2],其背后是人类对于机器人的复杂情感,如“弗兰肯斯坦”情结。
对科学及其创造物的恐惧一直是科幻小说的重要表达之一。这种恐惧既指向人类生存的外部环境,又指向人类自身,其中包含着对自然挑战的不安与对未来的担忧,这在第一部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中便可见一斑。在这部以人造生命为主角的悲剧中,“怪物”突破了人类自然的疆界,是“生命体和非自然物难以容忍的悖论”[3]153,从而招致迫害,而其创造者盗火的现代“普罗米修斯”也走向毁灭,双方以一种同归于尽的形式平息彼此的怨恨与同情,科学也成就了新时代“亵渎神明的恐怖故事”[3]150,而借“人造人”角色来探讨人性也成为科幻的重要主题[4]。
随着科学的发展,“劳动”被表征为“机器人科学”[5],人造人的幻想转向机械制造。“Robot”一词首次出现于剧作家卡雷尔·恰佩克的《罗素姆万能机器人》(Rossum’s Universal Robots)中。该词取自捷克语“robotnik”或“robota”,前者有奴隶、工人之意,后者则为单调沉闷的苦工、奴役的境况之意[6]。
于是机器人形象成为人类欲望与科学文化的投射。由于这些形象带有“服务性”“满足性”等特点,机器人便被置于较低的地位,因为在权力文化中,服务、满足他人总是低人一等,意味着妥协、不自由与被掌控。机器人也因此成为低地位群体的隐喻。但人类在道德上又无法容忍“奴隶”的存在,道德与欲望的矛盾难免引发冲突。
人类对机器人还有其他幻想。与上述低于人的地位相对的是人类对机器人“超人”能力的希冀。一部分人期望机器人能够超越人类的思维极限以更加接近世界的真理。他们无法接受人类群体的缺陷与恶,而崇拜至高的理性与最完满的善,而这种“善”也包含着完美的躯体。他们找到了实现柏拉图式理念世界的最佳载体,并将之作为人类进化的一环,开始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制造“超人”或说是神。安妮·福斯特(Anne Foerst)在《机器上帝》(God in the Machine)中认为,人类面对智能机器时会同时感到恐惧与被吸引,如同我们对神的体验一样,而科幻小说常将技术神圣化,并模糊了两者之间的界限[7]。
于是,低人的地位与超人的能力在机器人身上矛盾共存,这势必造成一些改变。阿西莫夫认为“取代”是人类对机器人感到恐惧的本质,因其是死亡这一“不可逆变化”带来的耻辱,“就像犹太拉比洛的人偶、弗兰肯斯坦博士创造的怪物……机器也是人类智慧的产物,它最终也将取代我们”[8]159。
人类用道德来缓解对他人的怀疑与恐惧,而阿西莫夫在科幻小说中提出的“机器人三大法则”,是使机器人“道德化”的设想,成为保证人类安全的重要设定,但遵循理性意志的绝对准则也难以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因其“与实际人类行为体现的模糊不清的伦理学大不相同”[9]。
在《……汝竟顾念他》(……That Thou Art Mindful of Him)中,机器人乔治第十认为人类只是众多生命形态中的一种,并与乔治第九进行对话以观照自身。它们从机器人的角度对“三大法则”进行解构,得出机器人比人类更像“人类”,因而应受到保护并主宰世界的论断。它们的推理基于这样的理性判断:当面对多个人类时,无论是服从还是保护都应选择心智、品格、学识上最优的人类,而它们比人类更像人类,所以赋予了自身主宰者的地位。此种看似绝对的理性有时是可怕的。
因此,即使有“理性准则”的约束,地位不对等下的力量失衡还是难逃悲剧。但阿西莫夫有其他方案,“还有一些关于机器人的想法是,机器人的发展不会走向超人的方向,而是更精细、更动人,向着人性化的方向发展”[8]144。于是,安德鲁的“非理性”成为他摆脱人类恐惧这一困境的机遇。
(二)机遇:非理性的机器人
机器人像是一个对照物,使人类得以反思自身。人类常以理性区分自身与动物,但机器人使人们意识到,使人之为人的,并不是理性,而是非理性,“人之为人的特性就在于他的本性的丰富性、微妙性、多样性和多面性”[10]20,而这些特性无法用逻辑加以分析。人类之所以可以与机器相区分,正是因为人类没有绝对理性,而是常常出现“差错”,“差错”在道德或其他价值体系有着别样意义。这也是人类在自由意识下做出选择的体现。对于人类来说,最理性的选择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择。
与其他机器人不同的是,安德鲁并没有严格设定好的程序,而是拥有一颗像人类一样具有不确定性的正电子脑,“设计正子径路的相关数学太过复杂,顶多只能允许近似解,因此我的能力不是完全可预测的”[11]514。这意味着,安德鲁并不是完全理性的,并具备了非理性的基础。非理性因素是个体难以预测的特性,也是个体间的差异所在,因其“带来个体思维及其结果的不确定性”[12]。
作为人类的老爷似乎更喜欢有着不确定性的安德鲁:“新的机器人不会起变化。他们专门执行设定好的任务,从不会走岔。我比较喜欢你这样子。”[11]500正因为安德鲁拥有了那些人类才具有的微妙、丰富与多样性,才能获得自由与为人的权利。而安德鲁自主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以希望变得与人一样,就是一种非理性的行为,因为在绝对理性下,自由意志并没有安放之地。以自身的死亡来结束他人的恐惧,这对安德鲁来说并不是个理性的选择,却是人性可以理解的选择,也最终使人类的认可与愧疚同时出现。
与其他科幻作品着力于刻画机器人的强与人类的弱不同,阿西莫夫笔下的安德鲁更展现了人性的温情。这部作品鲜少描述人类与机器人的具体冲突,更多的是安德鲁对自我的探索,也是人类对技术塑造自身的思考隐喻。阿西莫夫没有否定什么,只是提出了一种可能性。事实上,在阿西莫夫的诸多故事中,人类一直在接受与拒绝机器人之间摇摆不定,他们渴望机器人的帮助,又对机器人感到害怕,这一主题也贯穿于其短篇小说集《我,机器人》(I,Robot)之中[7]。
二、安德鲁“为人”的社会维度进路
(一)权利的争取
安德鲁尝试成为人,从追求自由权利开始。他十分清楚人的自由为何物,并懂得运用约束。他对自由的迫切是一种情感上的需求,特别是当他感受到“爱”之后,因为“自由是爱的先决条件,爱的存在概念必须定位于一个人的自由领域内”[13]。
更为重要的是,安德鲁拥有自由的能力,即使不依靠人类,他仍然能够生存,且不逾越人类的法律规定。他在艺术创作上十分有天赋,为马丁家族创造了财富,杰拉尔德·马丁让其拥有了银行户头与信托基金,这是一个法律权利上的先例[14],在一个资本运作的社会中,金钱是生存所必需的。安德鲁的第一个自由,是他用金钱买来的,以脱离仆人身份,“安德鲁的全部自由都是由理查德·马丁给的,自由的代价便是他被逐出了马丁家”[13]。
安德鲁的第二个自由是向法院争取法律意义上的自由权利。反对给予机器人自由的检察官认为,对于机器人,“自由”两字毫无意义,只有人类才拥有自由。人拥有天赋自由的原因是人是被“生”下来的,而机器人是被“制造”出来的。“生”是一个自然意义上的过程,“自然”的比“人造”的地位要高,这一思想源自人类对自然与造物主的崇拜。
安德鲁却认为,只有希望获得自由的人才能是自由身。法官最终认可了安德鲁的自由:“任何生灵只要拥有足够进化的心智,能领悟自由的真谛、渴望自由的状态,吾人一律无权将其自由剥夺”[11]503。如果自由之人妨碍自由,那自由便是矛盾又虚假的,如果自由只为某一群体所拥有,那便成了压迫。
安德鲁在要求拥有自由时,就已经彰显了他的自由意志与自由选择的能力。他大可以“自由”地生活而不向法律申求,只是需要伪装与隐藏起那自由的心灵。但他并不想要伪装,因为真正的人类不需要伪装。而且,他所追求的并不是真正的“自由”,而是人类文化所建构的自由。因为人类未必真正拥有自由,它是一个内涵不断变动且充满矛盾的概念,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在《论木偶剧》中认为,木偶反而拥有人类无法企及的自由,因其能够抵抗重力这一阻碍,而大多数舞者却不具备这样的素质,所以意识对人的自然优雅可能造成了破坏[15]3-5。由此可见,人与机器人谁更能自由并无绝对定论,“自由”对安德鲁来说只是成为人所需要的一个人类文化下的“概念”。
在社会生活中,自由在人类权利的互相让渡与约束下实现。在卢梭看来,天赋自由要被共同意志所限,公民与道德的自由在人们遵守共同制定的法律下实现并得到强化[16]。只有被法律承认后,安德鲁才拥有了人类意义上的“自由”。当老爷疑惑安德鲁仍要遵守机器人三大法则怎么能算自由时,安德鲁的回答是人类也受到法律的约束,安德鲁认可并接受人类的自由。
但获得自由权利后的安德鲁并没有获得马丁家族以外其他人的认同。当他尝试向两名人类问路时,便被要求脱去衣服甚至肢解自己。两人的命令使安德鲁的大脑嗡嗡作响,受机器人学三大法则的约束,他不能采用任何手段保护自己,因为第二法则“服从”凌驾于第三法则“自保”之上。直到乔治赶到后假装命令安德鲁进行攻击,才为他解了围。
于是安德鲁需要新的法律宣告机器人的权利,即不被伤害的权利,如他不能伤害人类一样。为了获得这一权利,安德鲁与乔治决定借助舆论的力量。乔治首先提出,安德鲁是人们的朋友,应该分享友谊的果实。其次,如果机器人不能伤害人类,那人类也不能伤害机器人,因为巨大的权利伴随着巨大的责任,应有法律与机器人三大法则相对应。此时,乔治已将安德鲁预设为了有意识的道德主体,以使人们对他产生因主客体间存在一致性而引发的情感认同[17]。
(二)语言与符号:融入人类精神世界
安德鲁另一个成为人的社会维度的尝试是与人进行平等的沟通互动。为了消除最初无法与人沟通的不自在感,他开始学习人类所使用的语言符号。他在研究机器人史的过程中深入思考了人类使用的符号,“‘令机’能不能比照‘令人’这样使用,或是‘令人’已经成了十足的比喻用法,与原本字面上的意义已经分家,因而对机器人同样适用?”[11]512。随着安德鲁与人的互动能力的增强,他从最初的服从到学会下命令,甚至开始撒谎、施加威胁,他学会了如何与人交流并达成自己的目的。
这对于安德鲁成为人有重要意义。当安德鲁与人沟通且能融入人的语言情境时,便拥有了进入人精神世界的钥匙。在莱奥帕尔迪看来,物质具有思考能力是一个事实,人类就是这一事实的体现,“人类这种动物就是会思考的机器”[15]46。在这种观点下,除了肉体与金属的区别,人类与安德鲁这样的机器人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
人类的精神世界由符号构成。除了物理世界,我们还生活在由语言、艺术、神话等文化彼此不断交融形成的符号之网中,“人是在不断地与自身打交道而不是在应付事物本身”[10]43。当安德鲁学习并使用人类符号之时,如跟人对话、撰写机器人史、创造艺术品等,就是在融入到人类的符号之网中,与人类共处于同一个精神与意义世界,“正是依靠这种基本的能力——对自己和对他人作出应对(response)的能力,人成为一个‘有责任的’(responsible)存在物,成为一个道德主体。”[10]11因此,安德鲁是有理由成为道德主体的。正如书中小小姐所言:“当你跟他讲话时,你会发觉他像你我一样,对各种抽象概念都有反应,这难道还不算吗?”[11]512
安德鲁在社会维度上的尝试为他赢得了法律上的权利。但这并没有解决最终的问题,他还是难以被认可为人,于是安德鲁开始了技术上的尝试。
三、安德鲁“为人”的技术维度进路
(一)以人造器官扩大“人”的定义
安德鲁的上述尝试为他赢得了部分法律权利,但他被认可为人却是通过技术手段实现的。安德鲁在技术维度上扩大了人的定义。
他首先尝试在外在形态上更加接近人类。他得知机器人公司已经掌握造出拥有纤维皮肤和肌腱的仿制人技术后,便要求将自己替换成有机体机器人。按“恐惑谷”[18]效应,这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人类对机器人的恐惧,极度的逼真还会使人类对之产生移情效应。
他自己也开始尝试做一名机器人生理学家。仿照人类获取能量的过程,他设计了可以从碳氢化合物的燃烧中产生能量的系统,及进行受控催化分解的燃烧室。如此一来,他便不再依赖原子电池。保罗指出原子电池可能更加优秀,安德鲁表示,“就某些方面而言,或许没错,但原子电池是非人的装置”[11]520。他要模仿的不仅是人类的外表,还有生存机制。
除了改造自身,他也为人类提供了改造方案,他敏锐地察觉到了人类的嫉妒情绪,并选择让双方在机体构造上逐渐趋同。他要求机器人公司制造有机装置,以使自身可使用有机能源,人类也可以利用有机装置保持健康。安德鲁后续又研究了处理固体食物的装置与肛门、生殖器等人体器官,如此一来,安德鲁失去了那些机器人才具有的优势,“你原本比人优秀,在你选择有机体的那一刻,你就开始走下坡路了”[11]523,但他与人类在生存机制上的差别变得微乎其微。
更重要的是,这在技术层面上扩大了人的定义,“发展出一些人造器官,使人类具有机器人的许多特性”[11]522。这让人与机器之间的界限变得逐渐模糊,人与机器的二元对立也不断消解。
人造器官的生产使安德鲁的律师事务所确立了不论人体内有多少人造物都依然是人这一事实。由此他们将舆论引向了“支持人籍的广义解释”[11]528,也就是使用人造器官仍然不会失去作为人的权利。人的定义被扩大了,同样使用人造器官的安德鲁应可以被纳入人的范围之内。
但棘手的问题在于安德鲁的大脑。人的大脑是有机体,由细胞构成,而安德鲁的正电子脑由人工铂铱合金做成。对于参照对象人来说,他的各个器官都可以用人造器官进行替换,除了大脑。一旦将大脑替换,这个人便不是原来的人,因为他失去了原有的生活经验与被塑造的“灵魂”,现代的精神性已经超越了物质性,成为自我定义的锚点。
于是安德鲁做了最后一个手术,使他正电子脑中的电位可以随时间缓慢流失,这意味着,安德鲁的大脑跟人的大脑一样可以死亡。而正是这一举动,使他在200岁时真正成为人类。从结果上看,技术维度相对于社会维度更具决定性。
(二)死亡:两种进路的交点
技术维度造成的“死亡”使安德鲁最终被认可为人,而“死亡”这一词汇有着双重意义,既指机体生命的停止,又指精神与意识的消逝。社会维度与技术维度在“死亡”这一点上交汇,共享了该词的意义。
人类要服从生理学法则,而机器人不用,它们只要定期更换零件与维修即可维持原貌,只要有足够的能源,它们确实能够永生。永久运转的机器是可以被接受的,甚至十分符合人类的效率观,但对有意识的机器人却不是如此。因为他们在外形、意识上如此像人,在生命上却与人有着根本区别,这正是人们难以接受的。永恒的完美在人类中心的视角下只能由人类完成:当一个机器人拥有意识时,则苛责其没有肉体;当动物拥有肉体时,则认为其没有意识。
于是安德鲁也发现了他无法成为人类的真正根源。人类也许会容忍一个不朽的机器人,但不会容忍不朽的人类,“因为唯有在放诸宇宙皆准的前提下,他们才能勉强接受自己生命的有限。基于这个原因,他们不会让我成为人类”[11]530。
由此可见,机器人的属性只对人类本身有意义。机器的形态对机器本身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它可以以任何形式存在,无论处于何种机体之中,它都可以正常运行。但当他被造成“人”的形态后,就需要背负枷锁与要求,这出于人类对机器人的矛盾态度。一方面,人类在意识到自身缺陷与人性的困境后,希望创造出完美的人造人,“或许阿西莫夫下意识地为我们创造了这种关于机器人的现代观念,正是为了将人类从自身最恶劣的冲动中解救出来,因为我们是一种如此粗暴蛮横、贪权逐利、自私懦弱且排斥异己的生物”[19];另一方面,人们却对这种“不朽的完美”充满恐惧与敌意。
前文曾提到,被“取代”是阿西莫夫认为的人类恐惧机器人的本质原因。而“取代”在阿西莫夫看来与死亡有着密切联系。他认为,人们习惯于如季节交替般的短期循环带来的长期不变性,而死亡这一“不可逆的变化”使人类永远回不到从前,且宇宙与他人不会一起消亡,单个的人最终被取代,而“这取代中隐含的侮辱更增加了死亡带给我们的伤害”[8]157,即使是希腊神话中拥有永恒生命与超人力量的神也难逃被取代的命运。而安德鲁的死亡,使他与人类一样可被取代。
除此之外,“死亡”对人类本身至关重要,人一生的意义在很多情况下是由死亡赋予的。如果人类失去死亡,那人类一生所追求的事物与价值都将被重新定义。海德格尔认为人的存在作为此在(Dasein)[20],而死亡是此在的一种存在方式,是不可超越的先行于自身的可能性。只有当人面对着行将到来的死亡时,操心与烦心才变得不再重要,从而面对其最本真的存在,真正关注自身的“生”,领会到生命的意义。或许,安德鲁只有能够死亡,即“先行到死中去”之后,才能真正成为像人一样的存在,并真正理解人类为何对机器人充满恐惧。
四、余论
安德鲁的非理性为他带来了无限可能,这是他能为人所接受的重要原因。而他在艺术、科学等方面的才能则为他提供了物质保障。他从社会与技术两个维度尝试成为“人”,在社会维度上争取自由与不被伤害的权利,在技术维度上使机器人与人类的生存机制更加趋同,从而扩大了人的定义,但最终使之成为人的是死亡,以真正消除人类对他的恐惧。非理性的选择与技术手段最终成就了想要成为人的安德鲁。机器人并不一定要超越人,而是可以成为人,进入到社会生活的体系中,并实现自身价值——就如普通人一般。而人类群体有着共同的福祉,在理想上朝着平等发展,人类要先信任自身,才能信任机器人。
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任何机体都生存于同一个盖娅(Gaia)[21]137之中,特别是人类世(Anthropocene)之后人与环境的关系更加紧密。即使是机器人也离不开地球能源,因此与人类一样是“地面人(地族)(terrestre;Earth bound)”[21]362。人类也在走向“赛博格化”,两者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达成共生关系。特别是在外部环境也逐渐“赛博格化”的进程下,人机共生的系统也已出现在后人类生存的视域下,而机器人将会是理想的协作者。
参考文献
[1] SŁAWOMIR K A. Paradoxes of Transrobotism:an Anti-Transhumanist Reading of Chris Columbus’s Bicentennial Man[J]. Roczniki Humanistyczne, 2018,66(11 Zeszyt specjalny):137-150.
[2] 程林 . 奴仆、镜像与它者 : 西方早期类人机器人想象 [J]. 文艺争鸣,2020(7):107-112.
[3] 达科·苏恩文 . 科幻小说变形记 [M]. 丁素萍,李靖民,李静滢,译 .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2.
[4] 余泽梅 . 赛博朋克科幻文化研究 [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20.
[5] 唐娜·哈拉维 . 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自然的重塑 [M]. 陈静,吴义诚,译 . 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2.
[6] REILLY K. Robots and Anthropomorphism in Science-Fiction Theatre:From Rebellion to Domesticity and Back Again[M]//WYNANTS N. Media Archaeology and Intermedial Performance. Cham:Springer Nature Switzerland AG,2019.
[7] GERACI R M. Robots and the Sacred in Science and Science Fiction: Theological Implication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J]. Zygon,2007,42(4): 961-980.
[8] 艾萨克·阿西莫夫 . 阿西莫夫论科幻小说 [M]. 涂明求,胡俊,姜男,等,译 .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2.
[9] 亚当·罗伯茨 . 科幻小说史 [M]. 马小悟,译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10] 恩斯特·卡西尔 . 人论:人类文化哲学导引 [M]. 甘阳,译 .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11] 艾萨克·阿西莫夫 . 阿西莫夫:机器人短篇全集 [M]. 叶李华,译 . 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1.
[12] 顾骏 . 人与机器:思想人工智能 [M]. 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8.
[13] KAHAMBING J,DEGUMA J J. Reflecting on the Personality of Artificiality:Reading Asimov’s Film Bicentennial Man through Machine Ethics[J]. Journal of Educational and Social Research,2019,9(2):17-24.
[14] SHORT S. The Measure of a Man?:Asimov’s Bicentennial Man,Star Trek’s Data,and Being Human[J]. Extrapolation,2003,44(2):209- 223.
[15] 约翰·格雷 . 木偶的灵魂:自由只是一种错觉 [M]. 于晓华,译 . 北京:新华出版社,2017.
[16] 罗伯特·沃克勒 . 卢梭 [M]. 刘嘉,译 . 南京:译林出版社,2020.
[17] 易显飞,刘壮 . 社会化机器人引发人的情感认同问题探析——人机交互的视角 [J].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21,38(1):71.
[18] 程林,江晖 . 跌入“恐惑谷”的机器人——从延齐与森政弘的理论说起 [J]. 中国图书评论,2018(7):35-43.
[19] 泰里·法沃罗 . 和机器人一起进化 [M]. 徐颖,译 . 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20.
[20] 马丁·海德格尔 . 存在与时间 [M]. 陈嘉映,王庆节,译 .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21] 布鲁诺·拉图尔 . 面对盖娅:新气候体制八讲 [M]. 陈荣泰,伍启鸿,译 . 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19.
通信作者:荆祎澜,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技术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