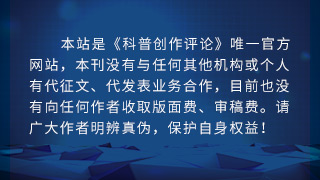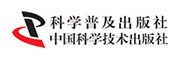引擎、链条与能源乌托邦
——评杰里米·威瑟斯《未来汽车与太空自行车:美国科幻文学中的路权争端》
科普创作评论
吕广钊
2024-08-09 12:44
一、石油的缺席式在场
自19世纪中叶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内燃机与化石燃料大规模用于社会生产,大幅提高了经济运行效率,直接催生了汽车的发明[1],而汽车也不负众望,在20世纪演变成某种“技术奇观”(technological wonder),被视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为重要的发明”,由此宣告了石油和汽车纪元的到来[2]。由于汽车的出现,城市空间与交通系统由此发生革命性变化,个人与世界的联系变得尤为紧密,资本主义加持下的工业社会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流动性”(mobility)。但是,这种流动性的代价却是全面而持续的环境污染。“19世纪末,不论城市还是乡村,都堆积着大量垃圾,充斥着空气、水和噪声污染”,人们忍无可忍,受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等作家笔下的风景和环境乌托邦的影响,“终于自发地产生了某种‘环境意识’的雏形;而在此之前,几乎没有人会对此加以深思”[3],只是将污染当作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副产品。
彼时,生态批评、毒性话语(toxic discourse)、人类世(the Anthropocene)等术语尚未出现,但毫无疑问,这些关键词在被概念化之前,就已经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无意识”[4]1-17,如幽灵般影响着人们认识、书写周遭环境的方式[5]。据陈文佳考证,虽然直观来看,作为基础性能源商品的石油,在美国小说中“存在感极低,与同样作为跨国贸易产品,并在殖民主义早期催生出大量文学作品的香料交易形成巨大反差”[6],但这并不意味着石油在美国文学中的失语。恰恰相反,经过两个世纪的发展,石油产业早已将触角伸入美国社会的各个角落,形成一种“能源无意识”[7],需要我们通过“字里行间的空白、断裂、沉默、犹豫等‘症候’……去重建‘被抹
换言之,在20世纪美国文学中,石油之所以“在场”,恰恰是因为它的“缺席”①。这样一种“缺席式在场”同样体现在20世纪为数众多的科幻作品之中,得益于科幻文学在书写或然性、可能性与潜在性时显示出的独特叙事潜力,人们对于石油滥用和环境污染的隐忧呈现为对于替代性能源的想象,将科幻文本视为一种“思想的试验场”,思考、推想并建构没有汽车、没有石油的能源乌托邦,而在这一过程中,电能脱颖而出,成为19世纪末乃至20世纪未来主义文学最常见的替代性能源。
1888年,美国乌托邦作家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出版了他最重要的作品《回顾:2000—1887》(Looking Backward:2000—1887),塑造了一个清洁、高效的电力乌托邦,刻画了一个电能驱动之下的“完美社会”[8]。在之后的几十年中,贝拉米笔下的电力乌托邦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文学母题,承载了众多作家、政客甚至工程师的能源无意识,以及他们对于“后石油”和“后汽车”时代的展望。1906年,美国通用电气工程师哈利·W.希尔曼(Harry W.Hillman)出版了一部未来主义非虚构作品,题为《展望:1912年无与伦比的电能发展》(Looking Forward:The Phenomenal Progress of Electricity in 1912)。书中,希尔曼从工业生产的角度,探索了普及电动汽车的可能性,并强调了电动汽车对城市空间的改造。“电力公司将在全市范围免费铺设充电装置,不遗余力地鼓励人们以各种方式使用清洁能源。”[9]而在1899年出版的小说《展望:1999年美利坚之梦》(Looking Forward:A Dreamof the United States of the Americas in 1999)中,作者阿瑟·伯德(Arthur Bird)描绘了一个听不到任何引擎轰鸣声的乌托邦社会,“在1999年,一个世纪前城市与乡村充斥的种种噪声完全消失……人们的耳朵不再为汽车和内燃机发出的巨响所折磨”,这些消耗石油的机器被悉数淘汰,“城市交通完全依赖电力供应”[10]192。伯德的畅想甚至比几年后希尔曼所描绘的更进一步,在他看来,电动汽车仍然有着提升空间,于是他构想了一种同样由电力驱动的飞行自行车(Ærocycles),骑行方式与传统自行车相似,却能够“轻松地在空中滑翔”[10]128,人们从此得以腾空而起,不必再忍受翻山越岭的身心疲惫。
虽然直到小说最后,伯德仍然没有解释这种飞行自行车的技术原理,他对人力驱动的传统自行车也抱有某种成见,认为它不够先进,不够卫生,也不够有效率[11]14,但在这部作品中,伯德明确指出了构想石油或能源乌托邦最重要的两个方向:替代性能源,以及替代性交通工具。近些年,许多科幻文学中曾经被忽略的元素都逐渐得到重视,石油无意识、能源无意识、物质无意识、人类世无意识等术语都已成为当下学术讨论的重点话题,现代交通工具催生出的“自主流动性”(automobility)和“自主的现代主体”(autonomous subjects)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起源,变成一种“中产阶级创造自我生活的方式”[12],而这样的流动性也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社会生产的组织方式,“在新左派式微、保守派抬头的后石油危机时代,削弱了劳动阶级的政治联合,为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新自由主义转向奠定了基础”[6]。
2020年,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英文系副教授杰里米·威瑟斯(Jeremy Withers)出版了专著《未来汽车与太空自行车:美国科幻文学中的路权争端》(Futuristic Cars and Space Bicycles:Contesting the Road in American Science Fiction,以下简称《未来汽车》),准确、适时地把握住了“替代性能源”和“替代性交通工具”这两个关键词,从环境人文研究(environmental humanities)和流动性转向(the mobility turn)的角度出发,正面回应了石油在美国文学中“缺席的在场”,全面梳理了19世纪末以来科幻小说对能源和交通议题的回应。一个世纪之前,福特汽车创始人亨利·福特(Henry Ford)曾自豪地表示:“我要造一种平民汽车……这种汽车价格低廉,每个工薪家庭都能承担,人们可以和家人一起,在上帝那辽阔的大地上纵情驰骋,尽享欢乐。”[13]在之后的一百多年中,这样的“纵情驰骋”深刻改变了人与人、人与世界的关系,但与此同时,汽车引擎能够带来多少便利,就能制造多少问题,它曾是科技、速度和现代性的象征,却又逐渐演变成现当代文学中能源乌托邦需要排斥、批判的首要元素。在《未来汽车》中,威瑟斯写道:“目之所及之处,美国科幻小说对于电动汽车和新能源交通工具的想象随处可见,这为我们探索、建构乌托邦社会指出了可能的方向。”[11]19他认为,“科幻小说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认识与‘流动性’相关的社会转变和技术革新,由此帮助我们回避(或者至少能够忍受)人类世带来的种种灾难”[11]7。整体来看,《未来汽车》采取了编年的结构,但威瑟斯所希望的,却并不是一部平铺直叙、按部就班的文学编年史。他首先讲了一个故事,将我们的目光引向一个科幻史上如雷贯耳的名字——雨果·根斯巴克(Hugo Gernsback)。

图1 《未来汽车与太空自行车:美国科幻文学中的路权争端》(利物浦大学出版社,2020年6月)
二、街道“封闭”之后:汽车对城市空间的重塑
自1945年开始,根斯巴克每年都会自费出版一本小册子,1951年正式定名为《预测》(Forecast),用以介绍他种种未来主义感极强的技术预言和科学构想,在圣诞节的时候分发给自己的亲朋好友以及学术上的合作伙伴,概不外售。在1955年的《预测1956》(Forecast 1956)中,根斯巴克写下《未来交通》(Future Transportation)一文,毫不掩饰他对美国汽车过剩和交通拥堵的不满:“迄今为止,人们没有提出任何有价值的补救措施,地上和地下停车场空间远远不够,而禁止汽车进入城市(尤其是外地汽车)又是一个政治和经济上完全不可能的选项,没有哪个市长会拿自己的前途去冒这样的风险。”[14]20世纪50年代,汽车产业在美国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根据美国摩托车协会(American Motorcyclist Association)和联邦公路管理局(Federal Highway Administration)的统计,在这10年中,美国年均汽车销售量达到590万辆(仅1955年就达到790万辆),截至1960年,有77%的家庭至少拥有一辆汽车,交通流量达到二战结束后的三倍[15],这一方面催生出美国在20世纪最狂热的汽车文化,但另一方面,人们也开始担心美国钢铁和石油供应能否满足无限膨胀的汽车产业,大规模交通拥堵引发了严重的空气污染,无处不在的大型广告牌和废旧汽车场也彻底改变了城市景观和空间结构[16],这些都是汽车黄金时代所必须面对的困境。
对此,根斯巴克在《预测1956》中给出了自己的解决方式。他并没有像很多保守主义者那样呼吁彻底取缔汽车,重塑旧有的田园乌托邦,而是继续践行他的技术乐观主义,设计了一种颇具未来主义色彩的两轮汽车,汽车中部安装了先进的陀螺仪,让汽车保持直立。这种汽车荷载四人,宽度却只有四轮汽车的一半,“生产时可以节省40%左右的材料,售价更低”,而且在外行驶时也可以节约40%的马路空间,“这无疑能够缓解当下街道过度拥堵的问题”[14]。在此基础上,根斯巴克甚至更进一步,给陀螺仪汽车添加了可折叠的飞行翼,构成了一种“飞行汽车”(airmobiles),所需的能源也并不是石油,而是“广泛使用的廉价原子能”[14],这在“后广岛”的冷战时代显得尤为大胆。对威瑟斯来说,根斯巴克的未来主义构想显示出强烈的“技术完美主义”(technological perfectibilism),他在《未来汽车》中评论道:“拒绝新技术并不是根斯巴克的风格……要解决汽车带来的种种问题,人类不需要解决汽车本身,而是应当运用更新的技术让汽车变得愈加完美。”[11]26-28

图2 根斯巴克在《预测1956》中设想的陀螺仪两轮汽车
实际上,根斯巴克的技术完美主义由来已久。他的立场非常坚定,甚至达到了刻板的程度。早在他1911年开始连载的《大科学家拉尔夫124C·41+》(Ralph 124C 41+)中,各种与“交通”有关的发明和新奇性(novum)设想便已经让读者应接不暇,包括电动汽车、小型飞行器、装了马达的旱冰鞋,甚至还有连接纽约和法国的跨大西洋海底电磁火车。在20世纪早期,根斯巴克作为《惊奇故事》(Amazing Stories)和《惊异故事》(Wonder Stories)的主编,对“纸浆时代”(Pulp Era,1926—1940)科幻作品的影响无出其右,他将自己的形象“烙印在1926年以来所有的科幻文本之上”[17],为20世纪30年代末兴起的“科幻黄金时代”奠定基础。不过,在威瑟斯看来,根斯巴克之所以对交通、能源等议题如此关注,并不仅仅因为他本身的技术完美主义。他在这一方面展现的个人偏好和兴趣之所以得到如此广泛的回应,也不仅仅因为他是知名科幻杂志的主编,而是因为在20和30年代,交通流动性与另外一个关键的社会议题产生了深刻联结,即“街道的封闭”(closure of street)。
威瑟斯指出,在这20年中,人们对于汽车和街道的认识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用‘技术的社会建构’领域(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y)的术语来说,在20世纪20年代,一种‘阐释弹性’(interpretive flexibility)开始影响人们对于‘街道’的定义”[11]30。自从古罗马时代开始,街道便是城市最为重要的公共空间,向所有人开放[18]9-12。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作为传统意义上“街道”的外来者和入侵者,机动车通常被视为一种昂贵却不必要的奢侈玩具,很少有人会因为汽车的出现而重新制定交通规范,而管理上的混乱也导致了严重的人车矛盾,交通意外造成的人员伤亡每日俱增。威瑟斯在1928年的《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中发现了一则不幸的旧闻:一名儿童因捡拾硬币被一辆出租车撞倒,不治身亡,而这名儿童,正是根斯巴克三岁的女儿[11]30。或许这就是根斯巴克对汽车产业和技术如此关注的原因?不论如何,关于“街道”的阐释最终在20世纪30年代重新归于“封闭”(closure),在无数汽车车主、经销商、制造商以及其他利益集团的宣传、游说之下,“汽车不再是无足轻重的奢侈品,而是现代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机器”[11]31。自此,行人将自己原本的“路权”拱手相让,被驱赶至街道两侧边缘的人行道,街道中心则被汽车彻底占领,成为独属于后者的交通空间。
在根斯巴克的影响之下,在“纸浆时代”,《惊奇故事》和《惊异故事》发表的许多小说都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这种关于汽车和街道的认识论转型。据威瑟斯观察,“这些文本描绘了以汽车为中心的城市和社会结构,讲述着人们的不满、痛苦,甚至死亡。不过,‘纸浆时代’的小说也都体现了强烈的技术乐观主义,相信科技进步终有一天会让汽车更适合我们的街道和城市空间,从而更适合帮助人类实现更幸福、更繁荣的社会”[11]31。除了类似《展望:1999年美利坚之梦》中塑造的能源乌托邦,城市空间也成为彼时科幻作者密切关注的话题。1928年,哈罗德·多尼茨(Harold Donitz)发表了短篇小说《来自20世纪的访客》(A Visitor from the Twentieth Century),小说中的建筑师马卡姆(Markham)为了准备参加一场奖金高达一万美元的城市规划大赛而疲劳入睡,睡梦中,受到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1899年发表的两部作品《当睡者醒来时》(The Sleeper Awakes)和《一个发生在未来的故事》(A Story of the Days to Come)的影响,他看到了他心目中完美的纽约城:巨大的建筑物为成千上万的纽约市民提供了住所,速度各异的移动平台(moving platforms)载着他们四处穿梭,“举目四望,我一辆汽车也看不到”[19]。在威瑟斯看来,虽然《来自20世纪的访客》用某种新的技术(移动平台)取代了汽车,但故事的核心依然与城市“流动性”紧密相关,更为重要的是,多尼茨的创作初衷,或许正是这种流动性在20世纪初带来的交通风险。多尼茨在小说中写道:
在我那个时代,行人被汽车挤到墙边,成批成批被撞死……出租车横冲直撞,这些司机受利益驱使,只学了最基本的几堂课便拿到了驾驶执照……他们夜以继日地工作,早就变成了机器人,根本无法承担起关照人类生命的责任。[19]
《来自20世纪的访客》对交通伤亡的描述可谓毫不夸张,根据历史学家彼得·诺顿(Peter Norton)的考证,在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有超过20万人死于交通事故……而在人口超过2.5万人的城镇,1925年因交通事故而死亡的人员中,行人占比超过三分之二”[20]。威瑟斯对这一数字深感震惊,进而联想到了乔治·麦克罗希德(George McLociard)1929年的短篇小说《马路杀手》(The Terror of the Streets)。故事中,发明家斯蒂芬森的未婚妻在一场交通事故中不幸遇难,悲愤交加之下,斯蒂芬森为了“消灭马路上的罪犯”[21],设计出一款无所不能的隐形汽车,比马路上任何其他汽车都更大、更快、更坚固,斯蒂芬森每天开着这辆隐形汽车四处巡视,寻找危险驾驶、不顾行人安危的鲁莽司机,在他们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之前,先下手为强,让他们丧失驾驶能力。
而在1928年的小说《原生人的反抗》(The Revolt of the Pedestrians)中,作者大卫·H.凯勒(David H.Keller)将汽车与行人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推演到了极致。在威瑟斯看来,与《马路杀手》不同,《原生人的反抗》没有采取“以暴制暴”的朴素伦理观,凯勒也不认为更先进的技术发明就能够解决城市流动性带来的问题。相反,威瑟斯认为,《原生人的反抗》体现了凯勒“对于汽车明确而绝对的反对”,这在“纸浆时代”的科幻作品中“尤为罕见”。小说的设定与威尔斯1895年的《时间机器》(The Time Machine)非常相似,人类因汽车而分化为两个物种。其中一个物种称为“汽车人”(automobilists),选择生活在金属的迷你汽车中,双腿也已退化,甚至与汽车融为一体,只有睡眠时才会短暂分离;而另一个物种则称为“原生人”(pedestrians),他们拒斥汽车带来的流动性,坚持传统的生活习惯,这招致汽车人对他们的迫害和屠杀,几近灭绝,只有少部分原生人逃出城市,在偏远山区或荒野幸免于难。但随着故事发展,原生人找到了汽车人的弱点,“他们开发出一项新的技术,将驱使物质运动的原子能抽离出来,只有人体肌肉不受干扰”[22]。于是,现代机械带来的流动性骤然间被瓦解,汽车人被抛弃在废弃的城市中自生自灭,用威瑟斯的话说,“他们仿佛被置于一间巨大的博物馆,警示全人类不要再走那条可怕而短视的汽车之路”[11]53。
不过,威瑟斯或许并没有完全发掘出《原生人的反抗》的文学潜力。这篇小说绝不仅仅是一篇警示性作品,它的出版也绝不仅仅为了反映“反汽车主义者”的不满,不管是从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的技术哲学、德勒兹(Gilles Deleuze)的生命哲学,还是哈拉维(Donna Haraway)或者布拉伊多蒂(Rosi Braidotti)的后人文主义哲学出发,我们都能在《原生人的反抗》中发掘出更为深刻的文学和哲学意义。但无论如何,自20世纪20年代,对于行人来说,街道的确是“封闭”了,它不再是向所有人开放的公共空间,而逐渐成为机动车和引擎的专属领地,城市的空间规划从此彻底改变。在奥特弗里德·冯·汉斯坦(Otfrid von Hanstein)1931年的《乌托邦岛》(Utopia Island)中,为了规避愈演愈烈的人车矛盾,城市被垂直分为十层,每层都部署了专门的交通工具,除了汽车,还包括地铁、轻轨、自行车等,而行人的活动区域在城市最上层。在威瑟斯眼中,为了进一步优化城市流动性,《乌托邦岛》并没有像根斯巴克的《未来交通》以及多尼茨的《来自20世纪的访客》那样借助更先进的技术,而是通过改良城市的空间结构[11]42,接纳汽车在现代城市的核心地位,从而接受街道对于行人“封闭”的既成事实。
三、自行车的反击:浪漫化的慢速主义
在对《乌托邦岛》中“多层城市”的讨论中,威瑟斯详细介绍了作品中关于自行车和自行车道的描述,由此联想到历史上一次著名的实验性市政建设——加利福尼亚自行车道(The California Cycleway)。在19世纪末,自行车的几项重大改良带来了一次来势汹汹的自行车热潮,与前轮大后轮小的老式自行车(penny-farthing)相比,新发明的“安全自行车”(safety bicycle)采用链条传动系统和充气轮胎,拥有更高效的齿轮比,可以使用更小的车轮,却不会因此损失速度。一夜之间,自行车成为某种社会风尚,社会保有量激增,为自行车设计专属的交通空间成为市政部门迫在眉睫的任务。
1900年元旦,连接帕萨迪纳与洛杉矶的加利福尼亚自行车道正式启用,全长约14公里。据史料记载,这条自行车道类似今天城市中的高架路,高出地面约15米,宽度足以容纳4名骑手并排骑行,每隔30米便架设一盏路灯以供照明。在最开始的规划中,自行车道沿途附近甚至还会建有赌场、饭店、咖啡厅、豪华休息室等娱乐和社交场所,形成以自行车为中心的消费综合体[23]。不过遗憾的是,虽然加利福尼亚自行车道广受欢迎,但却触碰到了铁路部门的核心利益,毕竟彼时火车的速度并没有比自行车快很多。于是,在铁路公司的游说之下,加利福尼亚自行车道在启用7年之后便被拆除,成为定格在史料中的影像和概念。

图3 加利福尼亚自行车道穿越帕萨迪纳
在威瑟斯看来,加利福尼亚自行车道的关闭,很大程度上也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美国自行车产业的缩影。自19世纪初发明以来,自行车在很长时间里都被视为“速度、进步、流动性和未来主义的象征”,这也重新塑造了人们对于“附近”的定义。但很快,自行车蕴含的进步性、流动性和现代性便转移到了汽车上。相比之下,汽车速度更快,行驶距离也更远,而自行车在短暂的繁荣之后迅速过时,退居人们对于19世纪的怀旧想象之中。换言之,自行车不再是与汽车平起平坐的交通工具,而被视为“低人一等的劣质品”[18]159,与行人一样被驱赶至现代交通体系之外。由此一来,自行车在社会生产中的政治经济价值也一并烟消云散,最终在一种“儿童化”(juvenilization)的过程中转变为孩子们的玩具[24]。如此背景下,威瑟斯指出,自20世纪伊始,“自行车在美国人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几乎完全消失”[11]61,也正因为此,“纸浆时代”科幻小说的未来主义想象大都以汽车为中心,自行车的地位无足轻重。但到了20世纪50年代的汽车黄金时代,科幻文学对于“或然性”的内在思考迫使科幻作者们重新发掘被汽车边缘化的“或然”政治经济结构和权力话语,自行车再次出现在人们视野当中,形成一股复古未来主义思潮[11]76,成为自20世纪中叶起至关重要的科幻意象。
1952年,罗伯特·A.海因莱因(Robert A.Heinlein)出版了《斯通家族的太空之旅》(The Rolling Stones),小说中,斯通家族是月球上的名门望族,但天才双胞胎卡斯特与帕勒克却对一成不变的月球生活感到厌倦,他们设法买到一艘二手太空飞船,打算飞出月球,在太阳系四处闲逛,顺便做点生意。威瑟斯强调,在某种程度上,尽管这部作品的叙事框架依然与汽车带来的“自主流动性”(automobility)息息相关,显示出“对自由行动的推崇和对远方的征服”[11]79,但海因莱因对汽车的态度却非常严苛,甚至略带嘲讽。他在小说中用了整整两页讨论了汽车的技术缺陷,认为汽车引擎效率低下,浪费能源,而汽车本身也由此成为“机械小丑的荒谬集合”[25]53。在汽车文化如火如荼的20世纪50年代,海因莱因反其道而行之,将汽车斥为“奴役了整整三代人”的“机械笑话”[25]54。
不过,对威瑟斯来说,《斯通家族的太空之旅》在科幻文学史上最重要的贡献,并不是对美国汽车工业的批评,而是将自行车重新纳入社会生产体系的范畴之中。故事中,卡斯特与帕勒克离开月球的目的并不是“旅行”那么简单,他们在飞船上装载了大量二手自行车,希望在火星上出售。他们认为,“在火星和月球的环境中,骑自行车的探矿效率要比步行高得多……对所有探矿者来说,骑自行车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在无法骑车的环境中,“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自行车扛在肩上,翻越障碍”[25]69。在海因莱因笔下,自行车俨然成为一种完美的辅助生产工具[11]81,效率高,功能多,适用性强,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环境诉求,且不存在技术垄断,这些都与汽车工业截然相反。更重要的是,海因莱因没有将自行车视为无关紧要的“玩具”,而是为其赋予了强烈的商业和劳动属性,用威瑟斯的话说,海因莱因重新建构起了“自行车的尊严”[11]83。他认为,《斯通家族的太空之旅》从未将自行车定义为仅有观赏价值的“怀旧景观”,而是不可或缺的社会生产要素,由此挑战了美国主流文化对于自行车的忽视和矮化。
此外,在自行车的内在“生产性”基础上,威瑟斯提到的“复古未来主义”还体现在另一个层面——速度。1969年,在厄休拉·K.勒古恩(Ursula K.Le Guin)的代表作《黑暗的左手》(The Left Hand of Darkness)中,由于严苛的气候环境,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里,动力交通工具在格森星上都无法快速移动。“在暴雪季节,除了滑雪板和人力雪橇之外,人们只能乘坐速度很慢的拖犁、动力雪橇以及穿越冰河用的漂移冰船。到了融雪季节,什么交通工具都不能用了。”于是,大宗货物的长途运输只能是在夏季,但即便如此,电力驱动的载货卡车也只以大概每小时30公里低速行驶。其实,“格森人完全有能力让车子跑得更快,但并没有这么做。如果有人问为什么,他们就会说:‘干吗要那么快?’这就像有人问起地球人,为什么他们的车子要跑得那么快,他们就会说:‘干吗不跑那么快?’语气同样不容辩驳”[26]。如此一来,格森人的交通习惯与20世纪中叶美国资本主义社会推崇的价值观格格不入,他们与地球人不同,不会追求速度、效率和所谓的进步,而是践行一种以自行车为模板的“慢速主义”②。
据威瑟斯考证,这样的慢速主义在科幻文学中还衍生出多种呈现形式。1951年,雷·布拉德伯里(Ray Bradbury)发表了短篇小说《徒步者》(The Pedestrian),并在两年后以这篇小说为基础,完成了他最著名反乌托邦作品的《华氏451度》(Fahrenheit 451)。《徒步者》中,在2053年,因汽车与大众媒体的高度发达,人们与现实世界基本失去了联系,他们出门就上汽车,回家就看电视,没有任何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主人公莱昂纳德·梅多(Leonard Mead)却是特例,他钟爱散步,愿意亲近现实和自然,但在这一天,一辆巡逻的自动警车发现了梅多,将他视为形迹可疑的罪犯,扭送至精神病院。于是,继大卫·凯勒的《原生人的反抗》之后,行人与汽车再次发生了正面对抗,不过这次对抗不仅仅是物理层面的空间争夺,更是权力和意识形态层面的压制和反抗。在威瑟斯眼中,《徒步者》中的汽车和加速主义所象征的,不再是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和查克·贝里(Chuck Berry)作品中的自由和冒险精神,而是“禁锢、偏执和监控”[11]71。因此,与之针锋相对的徒步和慢速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同时也被赋予了政治上的革命性立场。
当然,这种革命性的慢速主义还体现在很多其他作品中,包括1975年欧内斯特·卡伦巴赫(Ernest Callenbach)的《生态乌托邦》(Ecotopia)中的共享自行车、1992年尼尔·斯蒂芬森(Neal Stephenson)的《雪崩》(Snow Crash)中的机动滑板,还有1993年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的《虚拟之光》(Virtual Light)中的机动自行车以及旧金山—奥克兰海湾大桥上的临时社区。不过,在我看来,威瑟斯在《未来汽车》中最有价值的论述,在于他指出了“自行车革命性”的内在偏见。看过电影《时间规划局》(In Time)的读者想必不难理解,“慢速主义”本身也是一种特权。在威瑟斯看来,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美国科幻文学之所以借助“自行车”来想象替代性能源和替代性交通工具,并以此实现对汽车流动性和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反抗,正是因为自行车被边缘化、儿童化的历史。前文提到,在20世纪初的美国,自行车的政治经济意义逐渐消解,却因此承载起某种田园牧歌式的怀旧情感,作为一种文化符号,自行车开始成为童年、家庭和友谊的浪漫化象征,这在电影《E.T.外星人》(E.T.the Extra-Terrestrial)中尤为明显。
不过,威瑟斯提醒我们,这种浪漫化的符号具有强烈的种族和性别偏见。“历史上看,非裔美国人和其他有色人种难以负担购车和养车的高昂成本,很少有人拥有汽车,被迫只能依靠自行车、地铁、公共汽车等较慢的出行方式。”[11]166同时,由于汽车文化对男性气概的推崇,女性在汽车领域几乎处于完全失语的地位,甚至连儿童自行车更多时候也是与男孩的联系更加紧密。对少数族裔和女性来说,慢速主义非但不会带来解放,反而是一把枷锁。因此,奥克塔维娅·E.巴特勒(Octavia E.Butler)1993年的《播种者寓言》(Parable of the Sower)并没有像《徒步者》和《生态乌托邦》那样,通过替代性交通方式来召唤慢速主义的政治颠覆性。虽然小说人物的出行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自行车和徒步,但这种依靠与其说是自我选择,不如说是别无办法。正如主人公劳伦所说:“走路太痛苦了。我以前没走过这么多路,但我现在知道了……除了休息,没有什么能减轻疼痛。”[27]
尽管如此,《播种者寓言》还是为我们提供了后末世、后石油时代的替代性方案,“作为一种高度可靠的交通工具……自行车在石油消失之后,依然能够承担起重塑文明的重任”[11]168。在《人类世无意识》(The Anthropocene Unconscious)一书中,作者马克·博尔德(Mark Bould)列举了“人类世”另外的38个名字,“碳世”(the Carbocene)与“热力世”(the Thermocene)位列其中[4]7-8,由此强调了汽车引擎和化石燃料给我们星球带来的巨大影响。“新的术语代表新的故事,新的故事代表新的视角,而新的视角则能够赋予同一现象新的意义。”[5]
自环境和能源进入文学研究的视域之后,人们突然发现,“石油”似乎很少成为美国文学直接描述、追问的对象,但在《未来汽车》中,威瑟斯系统地梳理了20世纪美国科幻作品中替代性能源和替代性交通工具,认为石油的“在场”正是由于其自身的“缺位”。由此一来,威瑟斯从汽车引擎和自行车链条之中揭露了“石油无意识”,向我们展示了建构能源乌托邦的多种可能性。更重要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威瑟斯同时强调了科幻文学的现实取向和政治经济属性,虽然我们目前尚不清楚自行车、滑板甚至步行等出行方式是否会取得汽车内在的生产性,但电动引擎对传统内燃机的冲击却早已显现,是否能够实现汽车的“净零排放”(net-zero emission),成为作为共同体的人类文明走向能源乌托邦的关键。
作者:吕广钊,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讲师,中国科幻研究中心起航学者,研究方向为科幻文学、物转向等。
参考文献
[1] ECKERMANN E. World History of the Automobile [M]. Warrendale:SAE Press,2001.
[2] DOOLITTLE J. The Romance of the Automobile Industry [M]. New York:Klebold Press,1916.
[3] MELOSI M V. Effluent America:Cities,Industry,Energy,and the Environment [M]. Pittsburgh: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2001.
[4] BOULD M. The Anthropocene Unconscious:Climate,Catastrophe,Culture [M]. London:Verso,2021.
[5] 吕广钊 . 人类世的幽灵正在游荡——评马克·博尔德《人类世无意识:气候、灾难、文化》[J]. 科普创作评论,2023(1):25-33.
[6] 陈文佳 . 作为美国文学研究新方向的石油小说 [J]. 社会科学研究,2024(2):193-199.
[7] 陈文佳 . “能源人文”对文学研究对象和方法的重塑 [J]. 外国文学,2024(1):156-166.
[8] LIEBERMAN J L,KLINE R R. Dream of an Unfettered Electrical Future:Nikola Tesla,the Electrical Utopian Novel,and an Alternative
American Sociotechnical Imaginary [J]. Configuration,2017(1):1-27.
[9] HILLMAN H W. Looking Forward:The Phenomenal Progress of Electricity in 1912[M]. Northampton:Valley View Publishing Company,1906.
[10] BIRD A. Looking Forward:A Dream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the Americas in 1999[M]. Utica:I.C. Childs and Sons,1899.
[11] WITHERS J. Futuristic Cars and Space Bicycles:Contesting the Road in American Science Fiction [M]. Liverpool: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2020.
[12] HUBER M. Lifeblood:Oil,Freedom,and the Forces of Capital[M]. 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13.
[13] BURLINGAME R. Henry Ford:A Great Life in Brief[M]. New York:Knopf,1954.
[14] GERNSBACK H. Future Transportation[EB/OL].(1955-12-25)[2017-03-17]. https://archive.org/details/Forecast1956.
[15] WELLS C W. Car Country:An Environment History[M]. 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12.
[16] CHRISTENSEN D E. The Auto in America’s Landscape and Way of Life[J]. Geography,1966(4):339-348.
[17] WESTFAHL G. Hugo Gernsback and the Century of Science Fiction[M]. Jefferson:McFarland,2007.
[18] LONGHURST J. Bike Battles:A History of Sharing the American Road[M]. 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15.
[19] DONITZ,H. A Visitor from the Twentieth Century[J]. Amazing Stories,1928,3(2):170-177.
[20] NORTON P. Fighting Traffic:The Dawn of the Motor Age in the American City [M]. Cambridge:MIT Press,2008.
[21] MCLOCIARD G. The Terror of the Streets[J]. Amazing Stories,1929,4(1):18-36.
[22] KELLER D H. Revolt of the Pedestrians[J]. Amazing Stories,1928,2(11):1048-1059.
[23] FRISS E. The Cycling City:Bicycles and Urban America in the 1890s[M]. 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5.
[24] TURPIN R J. First Taste of Freedom:A Cultural History of Bicycle Marke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M]. Syracuse: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2018.
[25] HEINLEIN R A. The Rolling Stones [M]. New York:Ace Books,1952.
[26] LE GUIN U K. The Left Hand of Darkness [M]. New York:Ace Books,2000.
[27] BUTLER O E. Parable of the Sower [M]. New York: Grand Central Publishing,2000.
①陈文佳将石油的“缺席式在场”称为石油的“存在悖论”,强调石油“隐藏的普遍性”(hidden ubiquity)。她认为,虽然直接描写采油炼油过程的文本屈指可数,但加油站、汽车旅馆等石油产业链所带动的社会关系和文化逻辑却成为20世纪美国文学最为核心的特征之一,“因此,许多看似与石油无关的情节和语言往往暗藏玄机,而挖掘在场和缺席、表达和压抑之间的阐释张力,也成了解读石油小说的关键”。
②即便如此,在《黑暗的左手》物理上的慢速主义背后,是一种信息层面的加速主义。勒古恩设想的超光速共时通信设备“安塞波”(Ansible)贯穿她的多部作品,从保罗·维利里奥(Paul Virilio)的“竞速学”(dromology)出发,对人类来说,瞬时通信最后会带来某种信息爆炸,面对瞬间涌入的大量信息,人们失去了思考的能力,只剩下本能的反应,陷入了一种“实时的暴政”(tyranny of real time)。但威瑟斯认为,至少在勒古恩的小说中,安塞波仍然能够起到积极、正面的作用,减少了物理上的交通需求,降低汽车、飞船等交通工具的使用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