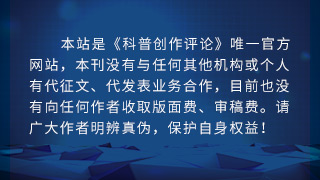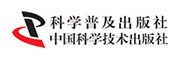1991—2006 年《科幻世界》科幻文学生产机制发展流变研究
科普创作评论
吕晨菲、方维保
2026-01-16 18:29
[摘要] 中国科幻文学在发展进程中呈现出与传统制度化文学及通俗商业化文学不同的生产特征。回顾中国科幻文学在1991至2006年这段时间的发展历程,《科幻世界》杂志及其旗下“新生代”创作群体实现了从生产机制到传播体系的范式转型:市场化运营策略重构文学生产关系,专业化作家梯队培育机制催生出新型作者队伍,图书出版工程的启动则让科幻文学生产走向商业成功。这一时期科幻文学生产模式的创新性突破不仅体现在商业维度,更塑造了具有时代特征的科幻美学形态。
中国科幻文学的演进轨迹呈现出显著的阶段性特征,其发展态势与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文化语境存在紧密的互文关系。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中国科幻出现了短暂的辉煌。从发表、出版渠道以及后续市场反响看,科幻小说走进了主流文学视野,不仅获得了文学制度和体制的接纳,更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科幻创作经历了从体制接纳到边缘化的结构性转变。科幻文学的属性争鸣[1]以及期刊出版行业自负盈亏[2]的政策导向,让科幻出版面临市场化转型的生存考验,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科幻文学的生产带来了挑战。
在此历史语境下,《科幻世界》杂志自1991年更名后启动的文学生产机制重构进程,具有范式意义。通过建构“新人培养—文本生产—读者培育”的三维互动模式,该刊成功推出了“新生代”科幻作家群体这一“明星作家”群体。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影响了小说最终的文本呈现,《科幻世界》以发行量的上涨证明其文化品牌打造与作家群体推介的生产策略是成功的,期刊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新生代”作家为期刊提供大量优质稿件,2006年《三体》的连载对于《科幻世界》来说更是此前未有、之后也并没有复制的里程碑式事件。但是,随着21世纪初网络逐渐普及,网络文学愈发具有影响力,来自文学市场之外的竞争也影响了读者在“文娱”这一项消费的选择①。《科幻世界》发行量一路回落并最终稳定在10万册左右②,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优秀科幻小说生产存在难度高、生产过程无法机械复制、难以拓展市场规模等问题。董仁威指出,在“新生代”之后,还有“更新代”科幻作家出现,“更新代”作家及其作品的发展,还需要时间的积淀:“从数量上看,要有足够多的作品,特别是长篇科幻作品,这样才能跳出‘科幻圈’,在社会上产生较大的影响。”[3]
一、《科幻世界》:制度建设与文化品牌生成
1984年,随着《国务院关于对期刊出版实行自负盈亏的通知》的发布,在主管单位终止财政拨款的压力下,社长杨潇接手《科学文艺》后的当务之急是让刊物生存下来。1984至1991年这段时间,是刊物维持经营、明确定位的探索阶段。杨潇在回忆录中提到,社方出品的《幼童科学绘画识字图片》(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年份不详,至少出版了5个分册)挣得数万元,而《晚安故事365》系列(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至1986年间陆续出版4个分册)则“前前后后印刷了大概80万套,光这套书就挣了80多万元”[4]18。这在当时无疑是一笔可观的收入。有了启动资金的《科学文艺》,还要为期刊经营的核心指标——发行量奋斗。1989年,《科学文艺》更名为《奇谈》,这是杨潇称为“吸引眼球”所作的尝试。尽管改名后的《奇谈》取得单期12万册的发行量成绩③,但这种“怪诞”的刊名使期刊“吃尽苦头”[4]38。最终,在读者来信推举的刊名中,编辑部选中了《科幻世界》这一沿用至今的新刊名。可以说,从《科学文艺》到《奇谈》再到《科幻世界》,刊名的变迁反映了这场艰难的转型。“科学文艺”包含的内容除了科幻小说之外,还有科学小品、科学诗、科教片等形式;“奇谈”则似乎脱离了“科学”这一重要元素而偏向了“哥特”或“志怪”等类型。最终于1991年定名的《科幻世界》证明了编辑部的决心,即以“科幻”为刊物主要内容来建设品牌。
改名后,《科幻世界》杂志社通过1991、1997年两届世界科幻大会(World Science Fiction Convention,简称WSF)的影响力回到大众视野,借助“银河奖”的文学评奖机制建立作家梯队,最终形成独特的文化生产闭环。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指出:“广告术中稳定的趋势,是把产品作为广阔的社会宗旨和社会过程的一部分来表现。”[5]1991至2000年是《科幻世界》树立杂志品牌形象、发行量走高的10年。在此期间,《科幻世界》杂志社的办刊方向即指向“广阔的社会宗旨和社会过程”。在“社会过程”方面,坚持办科幻大会、以银河奖发掘作者是其行动;在“社会宗旨”方面,服务科教兴国战略是其深层运营逻辑。
首先是“社会过程”。1990年,杨潇率代表团远赴荷兰争取到了1991年世界科幻大会的举办权,这是《科幻世界》作为文化品牌进入“社会过程”的起始。杨潇回忆:“杂志社几近砸锅卖铁地召开WSF 成都年会,为的就是由官方出面为科幻小说正名,为的就是宣扬中国科幻,宣传《科幻世界》。”[4]89从这次会议的规格可以看出,四川省政府、科协都非常支持《科幻世界》当时的努力。1997年,WSF在北京召开。如果说,成都WSF 让《科幻世界》增加了曝光度,那么这次的北京WSF 无疑是“扬名天下”:这届大会,既有时任中国科协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周光召致辞,亦邀请到了美、俄两国的宇航员出席会议,同时也有大量媒体报道大会的盛况。周光召院士在致辞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科技事业有了飞速的发展,科幻热潮也正在中国大地上兴起。为了促进中国与世界在科幻方面的交流,为了繁荣科幻创作,为了增进中国与各国人民的友谊,我们举办了这次国际科幻大会。古老的中国曾为人类进步作出过巨大贡献,现在,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正焕发出蓬勃生机,这次国际科幻大会在北京召开,更具有特殊的意义。”[6]这说明,进入“自主运营”时代之后的《科幻世界》仍然始终坚持为中国科技现代化出一份力——这无疑是具有社会担当的。这次大会的召开让《科幻世界》作为科幻小说发表平台重新回到社会过程之中,也让科幻小说得以被官方正名。不过,仅仅是一次“正名”还不足以让《科幻世界》实现作为一个文化品牌的商业成功。通过“银河奖”征文,《科幻世界》才真正拥有了自己通向商业成功的钥匙:“新生代”作家队伍,以及忠实的读者群。
文学奖作为现代文学制度的一部分,和其余制度性要素一样,深深参与了现代文学生产过程。王鹏指出,自1978年《人民文学》创办“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活动”以来,各种文学奖项及其代表的奖励机制促进了文学生产,并“逐渐成为了新时期加强和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进一步解放文艺生产力、繁荣新时期文艺创作、推举文坛新人、开创社会主义文艺新局面最为行之有效的重要方式”[7]。《科幻世界》主办的“银河奖”,也同样具有以上功能,如繁荣科幻文艺创作、推举科幻文坛新人、解放科幻文艺生产力等。“银河奖”推举的首批“新人”,与“新生代”作家群大致重合。1996年之前,“银河奖”的实际名字是“年度科幻文艺奖”;在1996年到2000年是“年度科幻银河奖”;至2001年开始,才直接称为“银河奖”①。奖项命名的逐渐变化,其实是广告术中的一种经典话语策略:“特殊的知识、立场、观点,往往会被它的生产者——特殊的社会群体有意或无意地普泛化,扩大到超出特定范围,具有超常的适用性和正确性”[8]。这一历时性演变揭示出地方性期刊构建全国性文学话语权的策略轨迹。经过杂志社的多年深耕,《科幻世界》在我国市场站稳了脚跟。在发表、评奖的过程中,《科幻世界》旗下的作品参与了社会过程。当时,《科幻世界》几乎成为刊发非儿童科幻小说的唯一阵地。在此背景下,“年度科幻文艺奖”所表彰的作品,已然可以代表当年“中国科幻”的最高水平。从“银河奖”获奖起步的作家,为《科幻世界》贡献了大量优质且具有“新生”活力的科幻作品。通过生产“新生代”“银河奖”这些和《科幻世界》强相关的科幻概念,发表具有较高质量的获奖作品,《科幻世界》终于凭借杂志品牌的成功打造,让科幻文学逐渐走出了低谷,重新回到公众视野中。
随后,《科幻世界》的版面调整与“押中”高考作文事件,则体现了社方始终努力跟随“社会宗旨”的行动。1995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提出在全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同月,江泽民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9]。《科幻世界》通过调整版面、刊发科普文章和更多的科幻小说等方式,力图跟随科教兴国战略进程。20世纪90年代初的《科幻世界》,科普占比较少,绝大多数版面内容是科幻小说和校园科幻征文,穿插一些介绍科幻历史的文章和国外科幻资讯。这段时间的《科幻世界》可以称得上是一本相当纯粹的科幻小说专刊。1997年,编辑团队发生结构性调整,期刊内容生产发生质性转变:刊物从单一类型文学载体转向复合型文化产品。其时,期刊开辟了封内彩页的科普图文专栏,不仅构成对政策导向的即时回应,更通过科学话语与文学想象的互文性书写,创造出独特的“科学人文主义”叙事范式。阿来②入职后,坚持在专栏中撰写科普文章,如《不要让科学疯狂》(1997年第4期)、《长生不老的梦想》(1997年第7期)、《数字化时代》(1999年第3期)、《寻找外星家园》(1999年第8期)、《关于生命的伟大发现》(1999年第10期)等。这些作品兼具细腻的文笔和坚实的科学知识,代表了该时期《科幻世界》发表的科普文章之最高水平。从文字编辑到担任主编,阿来以其在《科幻世界》的创作实践,将科普这一元素刻进了《科幻世界》的DNA,也为日后“硬科幻”审美占领高地提供了前期准备。这种转变,无疑是跟随科教兴国战略,保证整个《科幻世界》不与时代脱节所做的努力。
《科幻世界》1999年第7期刊登了两篇以“记忆移植”为主题的作品——阿来的科普文章《长生不老的梦想》与王麟的科幻小说《心歌魅影》。“记忆移植”这一主题恰好“押中”了1999年高考全国卷作文题“假如记忆可以移植”。在一次采访中,杨潇表示《科幻世界》在跟随时代潮流方面的努力是其“押中”高考作文的前提条件,“押中”的选题也正是对科教兴国战略的回应:“在变应试教育为素质教育的今天,素质中最重要的是创新能力。而读科幻,正是激发青少年创新能力的途径。”[10]“《科幻世界》押中高考作文”的消息无疑也是一次具有正向意义的品牌曝光——在2000年左右,《科幻世界》的发行量达到历史峰值,月发行量约36万册。相比最初“以书养刊”的窘迫,《科幻世界》凭借其自我构建的文学生产机制终于登上时代的潮头。在吸引大量读者的同时,也获得了丰厚的收入,保证了刊物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的良性运转。彼时,国内并非只有《科幻世界》在做科普工作,实际上还有相当数量的科普杂志在市场流通;科普并非科幻小说的核心任务,也并非《科幻世界》的核心业务,它是《科幻世界》的一种合时宜的“营销”手段。“押中”高考作文吸引巨量读者之后,如何留住这些读者?《科幻世界》这一文化品牌的核心产品仍然是科幻小说,作者如何生产小说?小说如何引人消费?《科幻世界》与“新生代”之间在创作方面仍然处在一个复杂的互动状态中。
二、“新生代”的文学生产:无法“真空”的文学创作
在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文学场域理论视阈下,“新生代”科幻作家的创作实践呈现出独特的“双元身份”特征。这批于20世纪90年代登上科幻文坛的创作者,普遍具有理工科教育背景与专业技术职务,如王晋康是高级工程师,刘慈欣是计算机工程师等。当然,童恩正、萧建亨、郑文光等“中兴代”中国科幻作家也存在此种“双元身份”特征,他们大多供职于高校、研究机构,具有扎实的科学知识。这种身份特征让他们能够广泛而灵活地运用积累的科学知识写作科幻小说。尽管都是“业余创作”,“中兴代”中国科幻作家的作品与“新生代”作家仍有所区别:“中兴代”作品中带有的鲜明时代印记逐渐消隐,个人意识于作品书写中日渐凸显。这种意识转变带来的叙事伦理、创作动机的变迁,体现在“新生代科幻”的文本当中,即呈现出全新的形态——文本既体现出“向内转”“个人化”的特征,又受到时代、读者、市场等因素影响。“真空”的、不受时代影响的创作是不现实的。
“新生代”创作整体呈现出的更加自由、“向内转”趋势,也出现在同时期的主流文学当中,例如以陈染、林白、徐小斌等女性作家为代表的“个人化写作”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出现,一定程度上说明“向内转”是该时期整个文坛的一种转变趋势。这种动机转变,让“新生代”科幻作家更多关注作品质量,向读者负责,写出自己的心声。例如,王晋康称平时经常翻看《人民文学》等纯文学期刊,写作最初是因为“读者”——家中孩子想听故事。韩松虽无理工背景,但他关于写作的看法是超然的:“每个人都有责任,把自己在这个片段宇宙中的经历,尽可能记录下来,留给另一个宇宙中的我看。”[11] 刘慈欣开始写作科幻的缘由更让人啼笑皆非——他在娘子关发电厂工作时,为了娱乐,经常与工友玩扑克,某次输掉整月工资之后,他戒掉了打牌,开始寻找新的“免费”娱乐方式,即写科幻小说。作者身份变化引发的创作动机转变一定程度上令作品呈现出刘慈欣所说的“空灵”的素质。
审视“新生代”作家发表在《科幻世界》上的小说,可以看出最终呈现的文本并非完全独立、“无功利”的,作家们发表的作品会受到现实的影响,进而改变作者后续创作。例如,星河、何夕、柳文扬等作家的部分作品以爱情书写为小说核心情节,而非以科学幻想作为核心情节。《平行》(1994年第6期)、《闪光的生命》(1994年第6期)、《决斗在网络》(1996年第3期)等作品均以“科幻+ 恋爱”模式写作,并且都获得了杂志社主办的各类科幻奖项。这种向写人性人情倾斜的科幻创作潮流并非孤例,美国科幻“黄金时代”之后兴起的科幻“新浪潮”,也更强调科幻小说的文学性。在20世纪90年代的“个人化写作”潮流中,科幻文学进行爱情书写是一种积极的尝试——它让“新生代”科幻的风格多变、更有“人的文学”气质,而风格多变的科幻小说也正是读者希望在《科幻世界》上看到的。
实际上,《科幻世界》杂志社方面也在尝试选择收录作品时关注到更广阔的意义空间。在《我与科幻》(1999年第7期)一文中,阿来认为其“最好的作品”是《科幻世界》杂志,他也指出科幻小说主要关注技术变革所引起的变化,由此可给科幻小说带来“巨大的意义空间”。而“最好的作品”是否超越了其代表作《尘埃落定》,这个问题几乎无法回答——毕竟杂志和小说是不同的媒介形式,但阿来将《科幻世界》视作“作品”而非“商品”,这样的表达方式隐含的观点是他将杂志经营和文艺创作这两件事等同,以一名作家、艺术家的审美标准来雕琢《科幻世界》这一“最好的作品”,并坚持进行科学普及。阿来引领的改革无疑是希望让《科幻世界》发表的小说作品整体质量向好发展。
在阿来发表此文的前一年,王晋康的《豹》(1998年第6期)夺得了当年的银河奖特等奖,它是《科幻世界》在整体文学性提升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该作品是此前罕有的分上下两部分连载的科幻小说,包含的内容更加丰富——基因工程、科学伦理、国际体育、种族问题、文化差异等议题隐伏在这篇小说当中,比之《亚当回归》等早期作品,《豹》更能体现王晋康本人提出的“核心科幻”观念。文本质量的提升固然离不开作者的个人努力,但阿来对文学性与科学性的把关也是推动其提升的关键驱动力。在《豹》于1998年夺魁之后,刘慈欣开始在《科幻世界》发表小说,并和王晋康一样连续多年在银河奖取得名次。仅1999年,刘慈欣就在《科幻世界》上发表了《鲸歌》(第6期)、《微观尽头》(第6期)、《宇宙坍缩》(第7期)、《带上她的眼睛》(第10期)。此后每年,刘慈欣均会在《科幻世界》上发表数篇小说,直至2006年《三体Ⅰ》连载结束。刘慈欣在回顾自身科幻小说写作历史时,将自己的创作阶段分为“纯科幻阶段”“人与自然阶段”与“社会实验阶段”。他认为,“纯科幻”的代表是《微观尽头》《宇宙坍缩》这样的作品——充满纯粹、空灵的科学幻想,离传统文学的要素较远。在最初的“纯科幻阶段”过后,他尝试向“人与自然”转向:“这种创作(纯科幻)是难以持久的。事实上,我在创作伊始就意识到科幻小说是大众文学,自己的科幻理念必须与读者的欣赏取向取得一定的平衡……我已经在做着这种努力,具体体现在《鲸歌》和《带上她的眼睛》两个短篇上。”[12]这也证明,尽管如前文所述,刘慈欣的作品带有“空灵”特质,但他的写作也并非完全“自由”“真空”的,也要考虑自身所处的文学环境、读者、发表媒体等要素。从“纯科幻”到“人与自然”,这种极具代表性的变化是文学产业剧变的时代注脚。
三、世纪初的革新:走向书刊结合的产业化发展
2001年12月11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对于国内的出版人来说意义非凡。这不仅意味着我们的文化产品可以走向全球,也意味着市场全面开放条件之下,国外的畅销书引进后会争夺国内图书市场份额。同时,从2002年的《中央宣传部、新闻出版总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的若干意见》到2003年的《新闻出版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再到2006年的《关于深化出版发行体制改革工作实施方案》,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系列政策的出台也让这个时期的出版行业开始经历转型,推动出版社“转企改制”[13]。和《科幻世界》关系密切的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以及重庆出版社①这一时期也开始了深化改革,这种改革,最终又影响《科幻世界》的“书刊协同”战略发展。在转型背景下,产生了和传统生产方式不同的新方式。邵燕君认为,传统文学生产方式与新型文学生产机制之间存在一种“分制”的关系。传统机制一般指作协- 文学期刊体制、专业- 业余作家体制等;而新型的生产机制则一方面需要借助传统的畅销书机制,另一方面需要以网络为主的新媒体文学生产机制。“传统机制对新机制的产生缺乏足够的孕育,新旧之间更多的是断裂而非反叛式继承。”[14]《科幻世界》在这个时期的机制也如此,是一种复杂的、新旧共生的状态。这种新生产机制,主要体现在《科幻世界》向“企业化运营”的转变。
杨潇回忆道,2002年的《科幻世界》已经开始了企业化运营:“杂志社实行公司制,实行总经理负责制。”[4]219这种转变,是《科幻世界》从“办期刊”到打造科幻文化产业链的开端。“新世纪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大众精神消费需求的扩大,文学和文化一起从‘事业’变身为‘产业’。”[15]具体至《科幻世界》的努力,则体现在版面调整和书籍出版两大方面。截至2005年,《科幻世界》杂志社旗下有《科幻世界·译文版》《科幻世界画刊》② 《科幻世界少年版》以及《科幻世界》等几种书刊,《科幻世界》无疑是其核心产品。对其产品的内容调整,读者意见是非常重要的参考。《十月,我们的精彩预演》一文提到了世纪之初读者调查的反馈结果:“本刊读者最大的期望是读到质量更高、数量更多、风格更加多样的科幻小说,特别是原创的中国科幻小说。”[16]这也代表了大量读者的心声。为了回应读者的期待,《科幻世界》在此后接连刊发刘慈欣、何夕、王晋康、韩松、星河、柳文扬等多位科幻作家的专栏,部分作家也曾在“银河奖”评选活动中获奖。除集中发表作品之外,还会附一篇作品评论。这既是一种增加科幻小说“浓度”的做法,也能够增加作者和作品的曝光度。这样,通过评奖、发表、评论等一系列期刊自主运营活动,“新生代”作家中的佼佼者逐步确立,这在“畅销书”大行其道的时代,是必要的品牌形象建设工作,也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作家作品的销售。
这一时期,为了推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同时也为了提升经济效益,《科幻世界》开启了图书出版工程。“中国自1992年起开始实行版税制度,到1993年、1994年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作家,尤其是作品畅销的作家都普遍要求出版社以版税付酬”[17]。但是,《科幻世界》杂志社已于1992年停止了此前以编书来维持杂志社运转的策略。《科幻世界》前总编谭楷回忆道:“1992年,《科幻世界》已经决定全力以赴办好刊物,以书养刊——即‘养鸡饲虎’成为历史。”[18]79当然,这里的“书”和之后出版的科幻相关书籍是两种类型。在1992至2002年这段时间,《科幻世界》不断地改版、征文、推举作家,将期刊自身质量提高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之后,科幻图书出版这一工作变得迫在眉睫。由于版税和图书的印数或销量直接相关,一本书如果能够畅销,出版方和作家均有收益。在2002年开启企业化运营并且集中发表了几位具有代表性的新生代科幻作家作品之后,《科幻世界》杂志社和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于2003年开始了一项规模宏大的图书出版项目——中国科幻“视野工程”。该工程计划在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持续推出引进的国外科幻与中国原创科幻作品,囊括“中国科幻基石丛书”“世界科幻大师丛书”“世界流行科幻大师丛书”等系列丛书。其中“中国科幻基石丛书”截至2023年已出版76部。
在“视野工程”之前,中国科幻小说绝大多数以中短篇形式存在。这从侧面反映出发表渠道上的限制——杂志发表科幻小说仍以中短篇为主。从内容来看,长篇小说更丰富,更有成为爆款IP 的潜力,但“长篇小说”出版比“短篇结集”更加困难。
以刘慈欣的《超新星纪元》为例,这部小说初稿完成于1989年,约30万字,是一部标准的长篇小说。1994年刘慈欣将该稿寄至《科幻世界》杂志社,其体量远远超出当时的《科幻世界》所能发表的作品体量。杨潇为《超新星纪元》的出版奔走,但由于各种原因“书没能出版”[19]。《超新星纪元》是刘慈欣向《科幻世界》的初次投稿,最终却以退稿告终。经历这次失败后,为了适应《科幻世界》的版面,他向杂志社投递了一些中短篇小说,最终成为中国科幻的“超新星”。阿来认为《超新星纪元》这部好作品不应该被埋没,于是他于2001年牵线搭桥,作品终“以‘锋线科幻’之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18]260。从这个图书系列的名字可以看出,作品具有“先锋文学”的部分特质。之后,《超新星纪元》再次经历修改,于2009年由重庆出版社出版,列入“中国科幻基石丛书”系列。2001年,刘慈欣接受《异度空间》采访,提到《超新星纪元》写作花费的精力“可以写十部《球状闪电》”,前后数易其稿、历经10余年。《超新星纪元》曲折的写作、发表过程固然和其文本的特殊性有关,但也和彼时国内缺乏出版长篇科幻小说的环境有关。“视野工程”对中国科幻小说创作尤其是长篇小说有助推意义——原创的长篇科幻不缺乏读者也并不缺乏作者,缺乏的是出版平台和持续的曝光。持续出版长篇科幻小说形成图书品牌,对促进中国科幻文学繁荣至关重要。
“视野工程”的启动某种程度上也向中国科幻长篇创作提出了需求。“在西方,科幻产业已经拥有完整而成熟的产业发展历史。纵览国外科幻发展史不难发现,科幻期刊发展到成熟阶段后必将带来长篇小说图书出版的突破,出现一大批畅销书,出现一批有丰厚收入的专职科幻作家。”[20] 可以说,长篇作品的突破是科幻文学产业发展的必由之路。2006年开始连载并最后结集出版的《三体》不仅是刘慈欣个人的成功,也是“视野工程”的成功。创作长篇小说已经从刘慈欣最初写作《超新星纪元》的自发模式,变成了自发和出版方策划等综合的多模式文学生产。《科幻世界》也形成了“投稿- 持续发表- 稳定创作- 获奖/ 单行本出版/ 合集出版”这一书刊结合的文学生产模式。对网络文学尚未兴起时的读者来说,认识新作家常常从《科幻世界》刊发其作品开始。在如今的文娱产业语境之下,“文学”更像是一种脚本性的产品——科幻文学IP对于科幻影视、游戏等而言是重要的脚本来源。《科幻世界》杂志社做好杂志本身与“视野工程”,具有开拓视野、挖掘科幻文学产业“基石”的意义。
四、结语
回望《科幻世界》从1991年到2006年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它不论是在艺术方面或是商业方面的探索都取得了成功。从1984年“自负盈亏”“自主经营”开始,刊名经历《科学文艺》《奇谈》最终于1991年定名为《科幻世界》,再到新世纪走向书刊结合的发展模式,杂志社在不断摸索中调整定位,打造中国科幻的主阵地。
《科幻世界》拥有这一时期最优秀的科幻作家群。刘慈欣、韩松、王晋康、何夕、星河、柳文扬……他们或发表短中篇,或出版长篇代表作,将中国科幻推向了新高潮。在作家自发创作之外,征文、组稿等以杂志社为主要定制方的工作也是这一时期文学生产活动的重要环节。以杨潇、谭楷为核心的初代《科幻世界》编辑团队和以阿来为核心的第二代编辑团队在这一时期的接力努力共同提升了《科幻世界》发表、出品的科幻小说质量,编辑与作者的共同努力让《科幻世界》成为中国科幻在世界范围内的“金字招牌”。
在过去,《科幻世界》和“新生代”共同建构了中国科幻文学在新时期的生产范式,产生了有影响力的文化品牌效应、风格兼容并包的“新生代”科幻以及随之产生的庞大科幻迷群体,共同造就了新时期以来中国科幻的又一次高潮。在市场环境风云突变、传播媒介多维化的当下,我们期待全新的科幻文学生产方式。
参考文献
[1] 吴岩. 科幻文学论纲[M]. 重庆:重庆出版社,2011.
[2] 国务院关于对期刊出版实行自负盈亏的通知[G].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85(1):11-12.
[3] 董仁威. 中国科幻名家名作大系[M]. 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2.
[4] 杨潇. 仰望星空:我亲历的中国科幻[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23.
[5] 马歇尔·麦克卢汉. 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 何道宽,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6] 周光召. 提前进入未来的科幻之旅——在'97北京国际科幻大会的致辞[J]. 科幻世界,1997(9):1.
[7] 王鹏.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D]. 南京:南京大学,2014.
[8] 庞菊爱. 广告文化力探源[J].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4(2):41-43.
[9] 江泽民同志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1995年5月26日)[N]. 人民日报,1995-06-05(1).
[10] 覃白. '99高考作文冲击波[J]. 科幻世界,1999(9):24-27.
[11] 韩松. 红色海洋[M]. 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
[12] 刘慈欣. 重返伊甸园——科幻创作十年回顾[J]. 南方文坛,2010(6):31-33.
[13] 张新华. 转型期中国出版业制度分析[M].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
[14] 邵燕君. 传统文学生产机制的危机和新型机制的生成[J]. 文艺争鸣,2009(12):12-22.
[15] 杨玲. 当代文学的产业化趋势与文学研究的未来——以青春文学为例[J]. 文艺争鸣,2010(17):124-130.
[16] 本刊编辑部. 十月,我们的精彩预演[J]. 科幻世界,2001(10):87.
[17] 邵燕君. 倾斜的文学场——当代文学生产机制的市场化转型[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18] 谭楷. 银河礼赞:我亲历的中国科幻[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23.
[19] 刘慈欣. 刘慈欣谈科幻[M]. 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
[20] 陈曜. 打开世界科幻之门的丛书[EB/OL].(2021-01-18)[2025-07-22]. https://www.chinawriter.com.cn/n1/2021/0118/c404080-32002298.html.
*通信作者:方维保,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中国现当代小说批评。fangweibao123@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