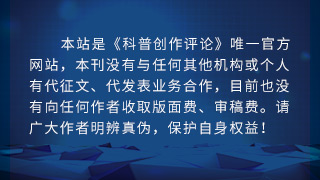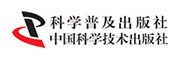走出记忆迷城
——《银翼杀手》系列中记忆叙事的文化哲思
科普创作评论
林伟
2026-01-16 16:49
[摘要] 记忆是《银翼杀手》与续集《银翼杀手2049》的核心哲学思辨主题。两部科幻片都通过记忆叙事来透视自然人/ 复制人的身份冲突,展现出“记忆叙述”与控制、身份想象以及道德能动性之间的密切关联,并突出了记忆的社会属性和“具身化”特征。两部影片以浓厚的媒介自觉突出了视觉影像在文化传承、记忆叙述和身份塑造中的关键作用,并间接指向了当下视觉权力的扩散以及由此引发的后现代记忆危机。影片独特的光影美学也隐喻着视觉媒介在文化记忆塑造、激活和重述中起到的关键作用,从而为当下科幻、记忆研究提供了一个思辨性视角。
科幻片《银翼杀手》(Blade Runner,1982)及其续集《银翼杀手2049》(Blade Runner 2049,2017,以下简称《2049》)都以未来世界自然人和复制人的冲突为叙事中心,探讨了人类身份、人工智能伦理、自我认知、自由意志、道德能动性等一系列哲学思辨议题。在两部影片展现出的纷繁复杂的后人类幻景中,记忆占据着核心位置。记忆是身份的前提,复制人瑞秋和K的移植记忆、德卡梦中的独角兽都隐喻着后人类境遇下的身份危机。记忆既是个人体验,也是一种文化景观。《2049》中枯死的树、橙色雾霾中的拉斯维加斯废墟是对过往时光的缅怀,也是一种触发集体记忆的场域。记忆源自个人生命体验和社会文化实践,也是一个动态的、需要编码和阐释的过程。“造忆师”安娜·斯特林博士基于自身的情感体验,将过往的美好时光虚构成一段段视觉影像,如记忆胶囊般植入复制人脑中,引导他们形成新的身份想象。在《银翼杀手》系列的科幻宇宙中,记忆虚构、生产、移植无处不在,渗透于城市空间中,可谓“后人类状况”的银幕显影——物种、文化疆界的崩塌和历史的断裂。影片的记忆叙事关联着其关键的戏剧冲突——人类与复制人的“疆界之战”。尽管亦真亦幻,记忆却构成了人类(包括复制人)生存所必需的身份定位标准,而复制人脑中的移植/ 媒介化记忆既是一种控制装置,也为自由和觉醒埋下种子。
记忆研究在当下文化研究中地位日益凸显。它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身份塑造、文化演变、历史叙述,以及当下社会新媒介对文化记忆存储、传播和重构的影响。《银翼杀手》系列的记忆叙事可谓一个思想实验,为当下记忆研究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正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所言,批判知识要有效地干预社会结构,就必须以某种叙事模式,通过间接的陌生化,让人们反思自身的绝对局限性[1]。《银翼杀手》系列正是在后人类语境下,通过复制人的身份话题,展现出记忆与控制、自主性、道德能动性之间的密切联系,并通过人物的身份建构过程,展现出记忆的交际性和“具身化”(embodied)特征。两部影片也以强烈的媒介自觉,凸显出当下视觉社会的记忆危机,以及影像媒介与记忆之间的交互建构性。
一、记忆、控制与身份设定
在西方思想史中,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哲学确立了思维/ 灵魂在人类主体性中的支配性,“人类身份”被与“灵魂”联系起来[2]。“灵魂说”身份观也构成了《银翼杀手》后人类宇宙中的权力运作法则,灵魂被视为区分自然人与复制人的关键标准。复制人是生物工程设计出并被批量生产的“产品”,因而被认为没有灵魂。在自由人文主义思想体系中,灵魂作为人类精神的象征,决定了主体的道德能动性(moral agency),即根据道德判断进行抉择、行动的能力。在前传短片《银翼杀手2036》(Blade Runner 2036,2017)中,生物工程专家华莱士下令让其复制人助手自残,以证明他设计的Nexus 9代复制人不具备自主性,是无条件听命主人的“好天使”。在片中的全球化资本架构下,“灵魂”成了维系社会秩序所需的边界划分和身份定义尺度。复制人被按照不同用途定制、生产出来,他们被理所当然地视为奴工,从事各种繁重危险的工作。为了赋予复制人一个完整的自我身份,泰瑞尔以及后来的华莱士公司在他们脑中植入人工记忆,以确保其精神稳定,从而顺从地执行各项任务。
在《银翼杀手》系列中,记忆既是身份的指示,也是一种控制装置。在前作中,泰瑞尔博士与负责追捕逃亡复制人的“银翼杀手”德卡会面时,向他解释了如何使复制人更好地运作:“如果我们赋予他们过去,就为其情感设置了一个参照对象,因而就更容易控制他们。”泰瑞尔公司为外星球殖民设计了复制人。他们比自然人更强壮,须通过内置的寿命限制进行控制。仅有4 年寿命的Nexus 6代复制人没有童年记忆,因此缺乏人类的共情能力。当复制人里昂在测试中被问及母亲的信息时,他突然情绪失控,杀死了测试者。因此,泰瑞尔在其后的Nexus 型号复制人脑中植入童年记忆。这些记忆虽然是虚构的,但与真实记忆无法区分。移植记忆为复制人提供了情感依托,也模糊了人和复制人之间的界限,需要专业测试才能分辨。可见,记忆和叙事在个人身份塑造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移植记忆给了复制人连贯、稳定的身份,从而保证了这些“产品”的正常运作。
《2049》进一步探讨了记忆与控制的关系。华莱士公司取代了泰瑞尔公司,改进了复制人的设计,但依然延续了记忆植入的做法,记忆也由此成为一种商品。影片围绕着复制人K对植入记忆的想象、阐释、重述,探讨了记忆在情感控制和身份认同中的关键作用。作为一名“银翼杀手”,K的任务是去追踪并“隐退”(即杀死)逃亡复制人。显然,作为一个有着情感认知能力的生命体,K不可能喜欢这份工作。然而他缺乏冲破设计代码的道德能动性,只能被动听命于系统。其中,他被植入的童年记忆起到了重要的平衡作用。K的自我身份定位与一段童年记忆息息相关。这段移植记忆描述了他在孤儿院的遭遇。他受到其他孩子的欺凌,被逼交出他心爱的小木马,迫不得已K只好将其藏进火炉,即使受到殴打也守口如瓶。由于自己的复制人身份,K一直认为这段记忆是被植入的。然而,这段甜蜜而酸楚的回忆不断浮现在他脑海中,成为他冷漠麻木外表下一颗温柔的种子。他在情感上非常依赖这段记忆,并不时地与智能投影女友Joi分享。
当K对自己的身份产生怀疑时,他来到“记忆制造师”安娜·斯特林博士的实验室寻求答案。博士说自己善于想象,可以创造出丰富多彩的记忆,而华莱士公司需要虚拟记忆以维持产品(复制人)的稳定性。对她个人来说,给复制人创造记忆是一种善举,因为他们生活如此艰难:“我无法帮助他们的未来,但我可以为他们创造过去,让他们甜蜜地回味。”这番话道出了记忆、控制、情感与身份塑造之间的互动关系。记忆在身份稳定性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特定的记忆赋予了个人身份连贯性[3]。斯特林博士创造的视觉化记忆也是对当下文化语境的巧妙隐喻,她的虚构记忆影像指向了视觉文化中记忆生成的心理机制。记忆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移植记忆给了复制人连贯的、可认同的身份,使其更好地听命于指令。稳定的身份需要浸润着个人情感的记忆作为依托。记忆犹如镇定剂,制约着复制人的行为,甜蜜的童年记忆给了他们精神慰藉,使他们安于现状。另一方面,基于真实情感基础上创造出的移植记忆也给了复制人共情的可能。而共情能力正是道德能动性的催化剂。K这段虚构的童年记忆不但给予他精神慰藉,也间接赋予了他道德抉择的自由。影片正是通过他的身份之旅来展现记忆的双重属性。记忆不仅赋予个体稳定的身份,进而达到精神控制和管理的目的,也不断在叙述中与个体发生情感互动。对于复制人来说,移植记忆不仅是控制工具,也是他们感知世界和定义自我身份的基础。
二、记忆、共情与身份重述
《银翼杀手》中,复制人瑞秋对自我身份的误认源自她对(植入)童年记忆的想象。《2049》则通过K的身份之旅探讨了记忆想象、共情和叙述在身份构建中的关键作用。个体对于自我人生的叙述在身份塑造中占据了中心位置。心理学家玛丽亚·谢赫特曼(Marya Schechtman)认为,“个人记忆和其他一些心理特性被整合到一个叙事框架中,导致我们的自传(自我讲述)决定了我们是谁”[4]。赵静蓉也指出,“记忆的核心问题就是重现”,也就是“基于某种现实情境的需要,有选择地征用、支配和占有那些材料,使其转化为与我们构建自身的主体身份相关联的、有意义的内容”[5]42。也就是说,记忆并非一个稳定的、一成不变的存在,而是犹如雾霭中的一点星火,只有在想象、叙述中才能成型。这种“记忆叙述”深刻地影响着个人的身份塑造和行为抉择。Nexus 6代复制人正是因为缺乏童年记忆,无法与新的个人经验形成连续性的身份。此外,对过去经历的回忆并非一个客观理性的过程,而是浸润着丰富的情感。个人记忆中的认知和情感功能是彼此交织的。封闭在个体意识中的记忆如同休眠的火山,只有当记忆素材与个体的情感发生互动和交流,记忆才会从意识的暗流中涌出。
与其他复制人一样,K被植入记忆,设定为执行任务的工具。虽然杀害同类的工作让他心存愧疚,但他始终安于现状。那么是什么触发了他的自主意识觉醒呢?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正是他的小木马记忆。更准确地说,是K如何定义自身与这段记忆之间的关系。电影暗示着,身份塑造并不取决于记忆真实与否,而在于如何对记忆进行想象和重述。起初,每当念及小木马记忆,K就会感到慰藉,纵然面对同类的憎恶和自然人的歧视,他也能保持情绪稳定。就此而言,小木马记忆是一种系统控制工具,使K能够更稳定地运行。然而,颇为讽刺的是,也正是他对这段移植记忆的重新想象和叙述,激发了他的道德能动性,促使他违背系统指令。
K杀死反叛复制人莫顿后,在附近枯树下挖出一具复制人女性遗体。检测发现她死于难产,而孩子的去向成谜。K在树根处找到一串看似出生日期的数字“6.10.21”,正与梦中小木马底部所刻数字吻合。他开始怀疑自己就是失踪的孩子。尽管孤儿院记录已被清除,K却意外地在废炉中找到了记忆中的小木马。随后,斯特林博士告知他,这段记忆曾真实发生过。于是,他开始相信自己就是记忆中的孩子,并非实验室制造出的产品,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爱的结晶。正是K对这段记忆的重新定义,激活了他强烈的身份认同渴望,促使他逃离系统。后来,他发现这段记忆是斯特林博士的真实记忆,她才是故事中的孩子。这段记忆既非完全的虚构,也非K的亲身经历,而是一段准记忆(quasi-memory),即以别人的视角和体验对真实发生情景的记忆。而这样的记忆片段,却能够在主体的身份叙述中形成一种粘合效应。稳定连贯的个人身份与感性记忆息息相关。在主体的自我叙述中,亲身体验的真实经历,往往附着有丰富的、彼此交织的虚构故事片段,犹如蒙太奇式的影像交叠。正是这些片段成为主体建构拼图中缺失的部分,有助于形成完整、连贯的身份和人格。对K来说,小木马记忆及其所携带的情感效应,成为其身份重述中的关键元素,影响着他后来的道德抉择。
此外,记忆并非仅仅关涉个体自身,也是一种社会交际现象。K的自我意识觉醒离不开他与AI 投影女友Joi之间的记忆共情。K和Joi都是后工业社会批量生产的科技产品,K负责追杀反叛复制人,Joi则作为虚拟伴侣为异性提供心理安慰。然而,他们在日常互动中却在不断帮助对方形成自我身份。K向Joi反复分享他的童年记忆,面对K的身份疑点,Joi也一再提醒他,枯树和木马上的日期吻合说明他是自然繁育的“生命奇迹”。可以说,Joi在记忆交流中帮助K将支离破碎的过去拼在一起。
认知心理学家丹尼尔· 魏格纳(DanielWegner)提出了“交互记忆”(transactive memory)一说:不同人的记忆系统是相互交织的,人们在处理和构建信息中可以发展出一种交互记忆系统。这种认知系统由关系密切的小群体组成,他们共同参与编码、存储和检索信息。成员们通过共享记忆片段,促进对方的记忆整合和叙述。[6]“与身份认同中‘他者’对‘自我’的建构相似,‘自我记忆’也要‘借助他人’记忆才能完成”[5]73,即通过主体间性的力量完成记忆元素的交流、补充与重述。正是K与Joi之间的交互记忆激发了他探寻身世之谜的渴望。他慢慢深信自己是个生命奇迹,一个天选之子,于是决定违背系统设定,踏上寻根之旅。就此而言,Joi作为人工智能和视觉媒介的结合,暗示着视觉社会中记忆技术的未来方向。
同样,K与斯特林博士也共享着一个记忆,她在孤儿院因小木马被其他孩子欺凌。这段记忆后来被移植给了K。这可被视作一种“替代记忆”(vicarious memory),即对别人经历的事件的记忆。即使主体自身并未经历过这个事件,由于深刻的共情体会,替代记忆变得非常鲜活生动,并激发主体强烈的情感和身体反应,指引其在社会互动中进行抉择。因此,即便K后来得知记忆中的孩子并非自己时,他与博士之间依然保持着深刻的共情体验,他能体会她的恐惧、痛苦和失落。他打破了复制人设计编码的限制,宁可牺牲自己也要帮助德卡父女相见。可见,K自主意识觉醒的关键并非小木马记忆本身,而在于K如何对其进行想象和重述。这也依赖于他与Joi的记忆交互,以及与记忆主体(斯特林博士)的共情。
一般来说,记忆,尤其是童年记忆,是支离破碎的,有赖于主观想象与叙述。个体对童年记忆的体验往往来自对图像和故事的叙述。记忆叙述是有选择性的,在筛选和省略中将彼此纠缠、抵触的元素整合成连贯的叙事。就此而言,复制人的移植记忆与自然记忆并无本质区别,被“植入”这一事实也不能成为虚假的标志,因为所有的记忆都包含,甚至源于对某个事件的转述和引用。在某种程度上,记忆是对过去事件的再创造。正如斯特林博士所言,“真实的”记忆不是一丝不苟地忠于事实,而是与对事件的“感觉”有关:“我们用感觉来回忆”,“任何真实的记忆都是一团糟”。可见,记忆叙述从来都不是对事件精确、客观的记录,而是浸润着感性的,对过去的再创造和想象。在《银翼杀手》宇宙中,记忆是脆弱的、模糊的,但也是个体身份叙事的唯一线索。在记忆叙述中,记忆主体的情感结构决定了记忆文本的阐释空间。因此,记忆主体无法触及“真实”的过去,而只能进入一个亦真亦幻的开放空间。个体对遥远往昔的记忆是一系列事件和印象的交织,并经由记忆主体来梳理和叙述。“记忆是人们借以获取过去经历的‘剧场’,是一个动态的中介场。受当前预期需要和信念的影响。”[7] 究其根本,K对移植记忆的移情和重述源自他自身的情感和身份认同的需求。
记忆犹如一个迷宫、一团浓雾,如何从中走出,取决于个体怎样处理与记忆素材的关系。K的寻根之旅充分展现出记忆和身份的交互建构属性。记忆和身份都处于动态变化过程中,其中不存在一个可被定义的“终点”。记忆主体的立场、情感态度、记忆方式都受到其原初身份设定的影响,而记忆的叙述、情感投入也会冲击主体身份的稳定性,从而生成新的身份。
三、记忆、媒介与具身触发
《银翼杀手》系列不仅强调了记忆在个人身份塑造中的关键作用,也阐述了个人记忆与媒介的关系。记忆既是个人情感参照,也是一种互文性文化景观,一种文化交流媒介。在《银翼杀手》系列呈现出的失忆宇宙中,夜幕下摩天大楼巨幕上的可口可乐广告和日本艺伎形象、档案馆的记忆球、橙色雾霾中的拉斯维加斯废墟、赌场中的自动点唱机……这一切构成了一个个“记忆场”,在与主人公和观众的接触中激活与过往的联系。可见,记忆并非一种静态的、单向的“事实”存储,而是一个流动过程,涉及编码、储存和再激活。荷兰媒介研究学者何塞·范迪克(Josévan Dijck)阐述了“媒介化记忆”(mediated memories)这一概念:“记忆不全存在于脑中,也不全存在于外界物质文化中,而是存在于两者之间,媒介化记忆在大脑、物质形态及其存在的文化环境之间不断进行着复杂的互动。”[8] 媒介化记忆是人类通过媒介对生活经历和日常信息的理解、编辑、提取和传播。正是媒介化记忆将个体与集体的记忆整合在一起,成为身份认同的关键参照。《银翼杀手》系列中的视觉记忆景观正折射出当下社会中记忆与媒介之间愈加密切的关联。
记忆不仅隐藏在个人的脑海中,还散布在世界上各种与个体生命经验相联系的物件中。这种集体性的、物质形态的记忆在个体身份塑造中起着重要作用。我们经常通过与照片、视频、书籍、信件、纪念品、衣服、艺术品等物品的互动来回忆过去的经历。社会心理学家雪莉·特克(Sherry Turkle)将这些称为“触发性物件”(evocative objects)。她认为,物件不仅具有实用性和审美性,也是一种情感交流和激发思想的媒介。物件是认知和情感的交汇,也是记忆的载体。看似无生命的物件和物象是社会文化实践的产物,在具体记忆行为发生前就已经凝聚着一段情感经验,而在与主体的移情互动中,激活主体自身的记忆存储,从而形成新的记忆经验[9]。
另一方面,记忆是基于某种立场和经验认知的基础上形成的符号化文本。记忆依赖于身体感知,是一个“以身体体验为内核,以世界作为‘他者’而构成的整体”[5]73。在记忆存储和激活的过程中,身体扮演了一个重要的媒介作用,身体在与物的交汇中存储、传递并塑造着记忆。因此,记忆并非纯粹抽象的,而是具身化的(embodied),根植于我们的身体经验中。家常菜肴的气味、熟悉的声音或手工艺品的触感都能激发强烈的个人记忆,创造出当下与过去的无形纽带。法国作家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 )中有一段著名的描述:主人公午后坐在椅子上,拿起一块玛德琳蛋糕,掰开一块蘸着红茶吃下。随着熟悉的味道在口中蔓延,旧时记忆的通道就此打开,儿时温馨的场景就在蛋糕和茶的气味之中荡漾开来。也就是说,玛德琳蛋糕触发了主人公现在的身体感受,从而激活了童年体验在记忆存储中留下的印记。
《银翼杀手》系列正是通过记忆主客体之间的互动,展现出记忆的具身与触发属性。复制人瑞秋对童年记忆的执念是一张母亲的照片,这个虚构的道具使她深信自己曾拥有真实的童年。她的自我身份叙述就是围绕着照片和植入记忆展开的。在K的身份之旅中,核心的触发物件是小木马。如果说枯树下的日期暗示着他与瑞秋之间的联系,孤儿院废炉中的实体小木马则真正诱发了他的记忆共情。当K触摸着小木马时,曾经亦真亦幻的记忆变得异常清晰,犹如他的身份叙述拼图最后缺失的一片,让他深信自己就是复制人繁育的天选之子。这种具身化体验成为叙事和现实交汇的关键,凸显出身体与记忆之间的物性关联。
当K离开洛杉矶来到辐射区寻找答案时,荒凉的、隐没在橙色薄雾中的拉斯维加斯废墟呈现出似曾相识的感觉。K步入废弃的赌场,穿过酒店大厅,而后在与德卡的搏斗中置身于旧时的餐厅。这熟悉又陌生的空间令他无所适从,此时空寂的舞台上陡然闪现出“猫王”(Elvis Presley)和玛丽莲·梦露(Marilyn Monroe)的歌舞投影,自动点唱机里流淌着往日的爵士旋律。在后人类的荒芜景观中,蓦然闪现的流行文化“触发影像”勾起了往日的美好时光,隐喻着历史、记忆和身份的回归。在人类文明史中,艺术、文学和音乐既是审美和娱乐,也扮演着文化记忆的载体,投射出某个特定年代的情感、价值和生命经验。建筑物、纪念碑更是承载着过往的盛衰和变迁。拉斯维加斯废墟犹如一段无声的证词,诉说着被遗忘的过去。赌场和酒店曾是奢靡的象征,而今却如幽灵般隐没在辐射区的雾霾中。颓败的建筑物犹如一个物理记忆库,封存着人类文明兴衰的痕迹。K在荒废赌场中的缓步游荡可谓一段具身化的时光旅程。废墟景观犹如一个陌生化的历史断面,在影片充满沉浸感的画面中,K在身体体验中触发了尘封的记忆。可见,记忆是符号化、文本化的社会建构,是一个开放式的叙事空间,而记忆的存储、解码和阐释必须通过个人身体媒介才能实现。
四、视觉媒介与文化记忆
《银翼杀手》系列是一场跨越35 年的思想实验,既涉及了“人”的本质、道德能动性这些本体论议题,也探讨了后人类文化边界纷争和身份认同问题。两部影片也以浓厚的媒介自觉突出了视觉影像在文化传承、记忆叙述和身份塑造中的关键作用。从前作中的巨幕影像,到续集中无所不在的全息广告、智能投影伴侣以及移植记忆影像,两部影片都间接指涉了当下视觉权力的扩散以及由此引发的后现代记忆危机。在当下社会,视觉媒介在个体生命经验和集体记忆中的地位不断凸显。文化学者扬·阿斯曼(Jan Assmann)对“文化记忆”概念进行了定义。他认为,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都希望“精神层面的内心和中间世界可以在时间的长河中固定下来,在其中寻找导向的回忆和期待、知识和经验的空间,并加以保存”[10]3。在此过程中形成的庞大复杂的符号世界就构成了“文化记忆”——“它着眼于赋予精神的内心和中间世界以稳定性和持续性,取消其易逝性和生命的短暂性”[10]4。
“后人类状况”意味着技术对身体、思维乃至记忆的侵入不断加深,而视觉媒介则构成了记忆的技术架构。如前所论,记忆的存储和激活是一个符号化的建构过程。记忆空间的开放性意味着记忆在叙述中不断被修改、补充和重述。在当下视觉社会中,影像在个人记忆叙述和身份塑造中起着关键作用,并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双向建构关系。视觉媒介可谓对现实环境的投射,而这种主观性的心理投射又会通过集体认同、文化记忆等方式,将自身携刻于现实空间中。劳拉·穆尔维(Laura Mulvey)认为,电影/ 视觉媒介与其生成文化语境存在着互动关系:“电影能够像雅努斯那样,既层叠渗透到周边的文化语境中,同时通过自身特殊的电影和戏剧形式,对其所在的文化语境进行视觉化呈现。”[11]也就是说,影像媒介与社会之间存在着一种共生关系。视觉意象犹如一种介质,提供了一种媒介化记忆,不仅向观众通过故事叙事的方式讲述某个年代的故事,更重要的是,通过其影像介质展现出电影拍摄年代的过往文化记忆。
《2049》记忆叙事的核心背景事件是2022年发生的“大断电”。一个反叛复制人为使同类免受追捕,用电磁脉冲摧毁了城市电力系统,所有的数字记录全被抹除,世界由此失去了与过往的关联。这一事件不仅是一个情节设置,更象征着一场集体文化失忆和历史断裂。人们只能从过往的物质遗迹中来触摸、想象历史。这也隐喻着当下社会对数字档案存储的日益依赖所引发的文化焦虑。大断电造成了集体失忆,而要向过去寻踪,则需要在个人与过往遗迹的具身化接触中对历史进行重新叙述、想象。当K在档案馆启动瑞秋的“记忆球”时,前作《银翼杀手》中德卡对瑞秋进行测试的残破录音片段响起。这可谓一个精巧的媒介自反隐喻:在一个视觉媒介社会中,记忆启封、再现并非简单地“叙述事实”,而是与视听媒介进行互动。如阿斯曼所言,历史的演进是“一种可以用文化记忆描述的连贯性,过去的意义被保存在文字和图像中,经过激活和重构,并入现有的语言模式中”[12]。“大断电”可谓一个关于历史和记忆的隐喻:文化记忆在历史长河中不断遗失,留下的只是过往时代的断章残简。正是基于这些残破的记录,历史和记忆又不断被后世基于其价值理念发现、想象和重述。就此而言,K的寻根之旅也是一场发掘过往历史,从而修复文化记忆的影像考古之旅。影片独特的空间美学传达出后现代视觉文化的屏幕(screen)/ 屏蔽(screen)矛盾性:大断电后的洛杉矶夜幕下,形态各异的全息广告飘浮在充满压迫感的摩天大楼群落中。凝重的巨型塔楼与颓败肮脏的地面环境构成了一种“垂直型隔离”秩序。而这也可谓一种视觉对立:交叠纠缠的混乱时空暗示着线性历史的断裂,以及记忆、身份的迷失。城市隐没在一片消费化视觉拟像之中,而真实的生活和记忆却被排除在外。这种“空间失忆”也指向了当下社会中的记忆危机。随着视觉媒介对个体生命经验的介入,个人和集体记忆都日渐融入视觉物象中,而人类自身的记忆能力不断退化。影像工业通过网络平台对当下生活深度渗透,制造出记忆繁荣的表象,然而无所不在的视觉奇观反而加速了人们的记忆遗忘。个人记忆隐没在商品化的信息洪流中,“被任意调用的数码影像以集体虚无的态度消解着个人记忆的历史意义……历史已被碎片化的影像无休止的重组所取代”[13]。
正因如此,K的个人身份寻根也是一场后人类社会的集体俄狄浦斯之旅,一次追回记忆、历史和身份的旅程。K对其身份之谜的执念源于他强烈的身份认同愿望。他不惜改变立场,驾着飞艇越过洛杉矶大城的围墙,穿过辐射区的雾霾抵达拉斯维加斯废墟。沉默的赌场遗址诉说着城市曾经的辉煌,勾起浓烈的怀旧思绪。过往建筑是历史的见证,也是集体文化记忆的物质载体。赌场废墟与洛杉矶凝重压抑的未来科技景观形成鲜明对比,使被遗忘的过去变得切实可感。赌场大楼中的流行文化影像则犹如一颗时空胶囊,一次过往历史幽灵的回访。影片由此展现出新媒介时代的记忆和身份危机,以及视觉媒介在文化记忆塑造、激活和重述中起到的关键作用。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幽灵性”理论认为,电影可以把过往的经验如幽灵般记录在胶片上,而放映电影则将记忆视觉化再现,犹如幽灵的还魂:“通过即时的、短暂的形象,克服时间和空间对于身体和知觉的限制。”[14]文字媒介的抽象性使其依赖于读者对语言的解码和意念重组才能实现文化记忆的传承,而影像媒介的直观性和“幽灵性”则可以在瞬间“击中”受众,触发其身体感知,进而打开文化记忆的通道。这段影像寻根也由此展现出视觉化记忆的双重特性:视觉奇观和影像碎片构成的信息洪流是对记忆深度的消解,而影像自身也构成了一种文化记忆载体。文化记忆透过物质中介能够超越时空限制,直接作用于个体的情感经验,进而构成对集体记忆的阐释。在影片呈现的后人类境遇下,视觉影像构成了最终的历史、文化救赎。记忆的触发与重述是一个符号阐释、重组的过程,取决于人对触发物件的具身化体验,而历史也是在主观记忆体验的过程中,被重新发掘,进而重新形成连贯的叙事,也就是“历史的记忆化”——历史和过往记忆本身难以触及,而影像提供了一种感知结构,成为后人再次叩访历史的窗口。
五、结语
《银翼杀手》的后人类宇宙中充斥着各种记忆形态——生物学自然记忆、技术化记忆装置、人工智能交互记忆、复制人移植记忆。这些记忆互相交叠、纠缠,并渗透到流行文化中,与个人和群体的身份认同发生着微妙的互动。两部影片的记忆叙事是一则凝重的关于历史与身份的寓言,为我们理解当下媒介景观提供了一扇思辨性的窗口。在一个文化记忆和历史叙述日渐媒介化的社会中,记忆和身份建构都处于无休止的流动过程中,无所不在的信息流使个体处于一种“数字化全景监控”中。文化记忆的工业化导致记忆和遗忘之间的平衡被打破,而短视频、网络直播等多元化动态影像日渐侵入个体的认知和自我言说之中。“信息过载”媒介生态使得个体被隐没在信息洪流中,丧失了思考的可能,从而引发文化记忆危机。两部影片都在自然人/ 复制人的身份本质探索中,重新审视记忆与身份、历史与影像之间的双向建构性。
参考文献
[1] JAMESON F. Progress Versus Utopia;or,Can We Imagine the Future[J]. Science Fiction Studies,1982,9(2):147-158.
[2] 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M]. 庞景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3] GOLDIE P. The Mess Inside:Narrative,Emotion,and the Mind[M].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
[4] SCHECHTMAN M. The Narrative Self[M].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
[5] 赵静蓉. 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6] WEGNER D M. Transactive Memory:A Contemporary Analysis of the Group Mind[M]. NewYork:Springer,1987.
[7] 邵鹏. 媒介记忆理论——人类一切记忆研究的核心与纽带[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
[8] VAN DIJCK J. Mediated Memories in the Digital Age[M].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
[9] TURKLE S. Evocative Objects:Things We Think With[M]. Cambridge,MA:MIT Press,2007.
[10] 冯亚琳,阿斯特莉特·埃尔. 文化记忆理论读本[M]. 余传玲,等,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11] MULVEY L. Death 24X a Second:Stillness and the Moving Image [M]. London:Reaktion Books,2006.
[12] ASSMANN J. The Mind of Egypt:History and Meaning in the Time of the Pharaohs[M]. JENKINS A,Trans. New York:Henry Holt and Company,1996.
[13] 刘汉文. 被重构的“真实”——后电影时代的影像记忆书写[J]. 电影新作,2023(3):28-37.
[14] 李洋. 雅克·德里达与幽灵电影哲学[J]. 电影艺术,2020(3):3-1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产学协同育人项目“人工智能背景下大学英语专任教师职业素养提升路径研究”(231106434135824);
广东省高校特色创新项目“‘两创’视域下中国科幻的话语本土建构与出海策略研究”(2025WTSCX190)。
*通信作者:林伟,广州中医药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电影研究、文化研究、英美小说研究。rayyain@gzucm.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