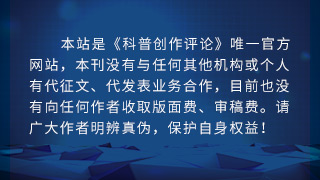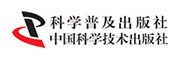科学童话的美学内涵与霞子的创作①
《科普创作》
孙桂荣
2020-06-22 20:31
在2018年度“中华优秀科普图书榜”评选活动中,霞子的《酷蚁安特儿总动员》(科学普及出版社,2016年版)从64种参选图书中脱颖而出,成为榜单中的10部作品之一,彰显了科学童话这一文学类型在当下的勃勃生机。的确,从1920年陈衡哲公开发表《小雨点》开始,科学童话便作为一个科学文艺的分支出现了。近百年来,经过历代作家的辛勤耕耘,已成为文学园地中一束艳丽的花朵,出现了高士其《我们的土壤妈妈》、方惠珍和盛璐德《小蝌蚪找妈妈》、郭以实《孙悟空大闹原子世界》、叶永烈《烟囱剪辫子》、孙幼忱《小狒狒历险记》、诸志祥《黑猫警长》等一系列优秀作品。霞子的《酷蚁安特儿总动员》就是在这一科学童话的发展序列中产生的,其不但丰富、发展了儿童文学创作,对青少年科学知识的普及更是起到了其他艺术种类难以企及的作用。

图1《酷蚁安特儿总动员》(科学普及出版社,2016年7月)
但本文要强调的是,科学童话尽管有着深厚的文学史传统与良好的读者接受土壤,但在概念界定、美学内涵等理论探讨方面还非常弱势和边缘,有些范畴谱系亦没有有效的厘定和澄清。关于科学童话的概念,1983年出版的《科普创作概论》中将其界定为“以科学知识为内容的童话,它要普及一定的科学知识并通过这些知识内容启迪儿童的智慧”[1],1989年出版的《童话辞典》中的解释是“科学童话用童话的形式向少年儿童传授科学知识,达到童话性和科学性的和谐统一”[2]。科学童话,顾名思义是将科学与童话相结合,但仅是这种宏观的概括,还无法说明其丰富与复杂的审美内涵。对此,霞子有过更为细致的论述。她将科学童话看成儿童文学中有别于“纯文学童话”的一类,并结合自身多年创作、阅读科学童话的经验,从想象美、纯真美、幽默美、象征美、荒诞美、悲剧美、喜剧美、知性美、自然美、逻辑美、简约美、镜像美、哲性美十三个维度探讨了科学童话的美学内涵[3],材料之丰富令人折服。
笔者认为,在这一问题上还有更深入探讨的空间。如“纯文学童话”借用的“纯文学”是在“重写文学史”潮流中被频繁使用的一个词语,主流文学研究界一直是有争议的,批评家李陀明确反对“纯文学”概念,张均则认为“‘纯文学’概念不符合文学生产的事实”,“纯文学”概念在过去和现在研究中存在“不纯”与无效的问题[4]。即使抛开纷繁的理论争论,在外界文化机制深重影响了文学内容、形式、刊发运作方式的今天,已很难分清哪些是“纯文学”,哪些不是“纯文学”了。因此,笔者认为对于那些更注重文学性、幻想性的童话作品不如以更平实的文学童话相称,以规避“纯文学童话”某些不必要的争议。科学童话与文学童话同属儿童文学的范畴,与纪实性儿童读物相比,它们都有幻想性、传奇性的一面,但文学童话更多诉诸儿童精神、情感的启迪与濡染,科学童话除此之外还有知识性、科学性的熏陶。当然,概念之余,还有些问题需要处理,如科学童话中科学性与童话性该怎样结合,如何处理科学童话与一般科普作品、文学童话之间既有区别又不乏联系的美学边界?在具体创作中又怎样体现出科学童话的独特美学意蕴?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探讨可谓辨析科学童话的中心环节,也是破解科学童话理论研究薄弱原因的关键之处。下面,本文结合霞子的科学童话创作对这些问题做具体论述。
笔者强调科学童话的儿童性。“儿童性”看似是科学童话不证自明的一种属性,但事实上,因为科学童话的作者一般是成年人,与作为受众的少年儿童之间有着明显的年龄差,要创作出真正践行“儿童性”的作品并不容易。评论者崔昕平曾言:“由成人书写‘易’于儿童并‘益’于儿童接受的文学,构成了儿童文学创作的最大难度。”[5]特殊的受众群体决定了科学童话同文学童话一样必须具有明确的对象意识、儿童意识。如何从成人视角俯视性书写的“为儿童”写作,转为蹲下身来以平视、对话的方式“作为儿童”来写作,可以说是童话写作者不能回避的首要问题。霞子的创作就牢牢把握了让孩子们喜闻乐见这一关键。在叙述方式的选择上,霞子的作品没有采取有些文学童话使用的第一人称叙事、回忆性视角的手法,而是以第三人称全知叙述的方式、简洁明快的语言,在开头三言两语就抓住了小读者的心。像《安特儿出世》是这样开头的:“森林边,坐落着一处小院。院子的后花园里,有一棵老爷爷似的大树。树下,住着一家子安氏蚂蚁。”《北极,有个月亮岛》中则以“北极,格陵兰岛东岸,接近北纬81度的地方”开头。这种叙事风格某种程度上更有利于科学童话以童话的方式普及科学知识这一精神主旨的达成。相对而言,文学童话的第一人称叙事让人有亲切自然之感,有利于创造妙趣横生的艺术形象。但是,第一人称是一种限制性叙述视角,像杨红樱的《笑猫日记》系列让笑猫充当叙述人,描述的是笑猫(“我”)眼中所见、耳中所听、心中所感的世界,即一切的言说均须经过日记主人视线、口吻、感知的中介。这对于尚负有科普任务的科学童话来说,可能会造成某种无形的制约,因为一部作品中的科学知识往往是以分散的方式分布于艺术形象与情节中的,单一的言说视角难以提供有效与足够的视点支撑。霞子的《酷蚁安特儿总动员》系列涉及很多蚂蚁知识,像铺道蚁为何要背着食客蚁行走、蚂蚁为何会出现夜游现象、蚂蚁若是没有了触角怎么办等。这涉及各种各样的蚂蚁类种,用一只单个蚂蚁的叙述视点是很难表述清楚的,频繁的视角越界不但会破坏相应的文体规约,而且会在一定程度上偏离小读者阅读接受能力。所以,霞子的科学童话采取了更易于孩子们理解的第三人称叙述方式。时间、地点、人物及动植物的情节背景交代得清清楚楚,有效地体现了科学童话的儿童性品格。
科学童话的文学性也与一般意义上的文学童话的文学性存在着微妙的差异。童话的文学性主要体现在幻想性、虚构性层面,不过科学童话与文学童话的幻想性、虚构性在艺术想象的设置、尺度等层面亦不尽相同,后者也会涉及具体的动物、植物等,也会有变形、奇幻、瑰丽的非日常化情节,但其一般是为象征、隐喻的修辞氛围服务的。像日本作家安房直子的童话作品《蓝色的线》,其中有关于织巢鸟、紫薇树、翻花鼓、金桂、艾蒿等注释,动植物被写入了文本,但这些都是为女主人公因为思念一个臆想中的人变成一只鸟这样一个奇幻的故事服务的,作为核心意象的“鸟”远远超出了现实中的织巢鸟,其美丽、神秘、妖娆、诡异给小说带来了凄美梦幻的色彩。文学童话对动植物等的浪漫化描述,是可以超出科学范畴进行一些夸张、荒诞、变形处理的,这是文学童话的美学类种决定的。对于科学童话来说,当然也需要虚构、想象,但涉及动植物时需要在书写对象的样貌、习性、特征范畴内进行合理的想象,以使给小读者传达的东西既是生动有趣的,也是能经得起科学推敲的。在这一层面上,霞子为科学童话的书写做出了榜样,如她的《神奇的“鸟叔叔”》也写到了鸟,而且是在“进行了近半年的刻苦学习和消化的前提下才下笔创作的”,她“为确定黑尾蜡嘴鸟是一年换一次羽毛还是换两次羽毛这样的细节,到很远的地方去请教养鸟人”[6]。在这样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烛照下,其童话创作没有像《蓝色的线》那样脱离织巢鸟本身进行“无边”的浪漫化书写,而是将奇趣和幻想牢牢建立在各类鸟知识的现实基础上。像放羊娃通过指哨与黑尾蜡嘴美羽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且互相救助的情节,虽充满童话般的幻想意趣,却是来自真实的自然传奇。

图2《神奇的“鸟叔叔”》(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12年5月)
至于科学童话不可或缺的科学性方面,也不能机械地理解。在其将科学的理性知识化为幻想的感性形象,或者说科普知识的“文学化”过程中,没必要、也不可能像系统的科普读物那样针对言说对象做面面俱到的知识介绍。也就是说,科学童话在涉及科学知识的传播层面自然是严肃的、有根有据的,但其并不对知识的系统性、完整性负责,抓住科学知识的某一点做艺术的形象化处理就行了,过分拘泥于知识的介绍甚至会适得其反。根本上讲,科学童话对文学趣味性、情感性的需求是第一位的,科学知识的穿插要服务于此,而不是让它们为科学服务,这是科学童话与一般意义上的科普读物最大的区别。像家喻户晓的《小蝌蚪找妈妈》并没有对小蝌蚪为何与青蛙不一样进行多少正面的细致描述,重点讲的是小蝌蚪找了鸭、鱼、乌龟、白鹅等很多动物,但都不是它们的妈妈,这是烘云托月、曲径通幽的文学性笔法,伴随着“妈妈妈妈你在哪儿”的深情呼唤,将童话的情感渲染与美学张力推向了高潮,最后以“来了一只大青蛙”收尾,让小朋友在意外的惊喜中自己去体会青蛙为何会是小蝌蚪的妈妈。假如叙事以虚构的方式正面描写小蝌蚪成长与变成青蛙的过程,便是一种拟人化的科普宣传,童话的艺术魅力就会大打折扣。在这方面,霞子的创作也是匠心独运的。在她的写作中随处可见抓住科学知识的一点为由头渲染铺排,以塑造生动鲜活的艺术形象与妙趣横生的故事情节为中心的特征。像她的《来自宇宙的水精灵》并没有书写复杂、深奥的水知识全貌,只是通过天一这个可爱的水精灵的指引,描述了易逗逗、李子明、胖宏三个性格迥异的小学生穿越时空,幻游都江堰、大运河、清明上河图的片段,在设置穿越时空这一奇特情节时,小说也没有做过多的其他渲染,只是紧扣天一的水精灵魔法而来,“只见天一小手一弹,一颗晶莹的蓝色水珠朝他们飞来,‘呼啦’一声,一扇古老的城门顷刻出现在他们眼前”“天一用小手悄悄一弹,一颗水珠飞向天空,蓦地出现了一个极现代的钢铁大门”。这种写法简单明了,易于为小读者所接受,水知识的点点滴滴穿插在小学生幻游场景与环保写实之中,保证了童真、童趣的文学性在场,这是科学童话能够为小读者所喜闻乐见的根本保障。
茅盾先生曾感叹,“儿童文学最难写,试看自古至今,全世界有名的作家有多少,其中儿童文学作家却只寥寥可数的几个”。可以说,在主流文学体制中儿童文学是被边缘化的。而在儿童文学中,相对于文学童话,科学童话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被边缘化的,像经常被提及的儿童文学大家,无论是西方的安徒生、格林兄弟,还是中国的冰心、曹文轩等,基本都是以文学童话著称。事实上,科学童话因为在给小读者审美享受之余,还能提供一定科学知识,社会价值与发展前景都是不可限量的,霞子的创作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作者简介
孙桂荣,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参考文献
[1]章道义,陶世龙,郭正义.科普创作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154.
[2]张美妮.童话辞典[M].哈尔滨:黑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1989:21.
[3]霞子.科学童话审美初探[M]//汤寿根.科普美学.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2016.
[4]张均.当代文学研究中的“纯文学”问题[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02):118-122.
[5]郑伟.如何建立儿童文学的高度[N].文艺报,2018-10-29(003).
[6]袁建国.霞子动物童话系列编辑感悟[J].中国编辑,2013(06):66-68,71.
①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从新时期到新世纪:女性小说叙事形式的社会性别研究”(19FZWB032)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