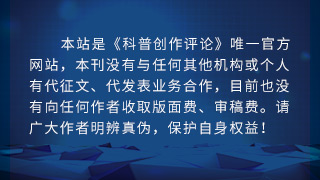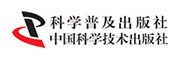阿瑟·斯顿巴赫将曲线球带到火星
《科普创作》
金·斯坦利·罗宾逊 著 李光辉 译
2018-01-28 14:42

(姚大海 绘图)
他是一个身材高挑、瘦弱的火星小孩。他害 羞,佝偻着背,笨拙得像只刚出生的小狗,真不 明白他们为什么让他打三垒。我是个左撇子,并 且不能接滚地球,他们却让我当游击手。但考虑 到我是美国人,这么安排也就不奇怪了。通过视 频学习一项运动就会带来这样的结果:有些事情 太明显了,以至于人们在视频里从不提及,比如 不要安排左撇子做游击手。但在火星上,他们正 在塑造一个全新的运动。有些人已经爱上了棒球, 他们购买了装备,试了几次后就开始了。
所以就这么开始了,我和这个名叫格雷戈尔 的小孩负责对付内场的左侧。他看起来很小,我 问他年龄,他说八岁。我心想:嘿,你可并不太 小。但我很快意识到,他的一年是火星上的一年, 所以他大概相当于我们的十六七岁,但显得更小 一些。他是最近从别处搬到阿吉尔(Argyre)的, 和亲戚还是朋友住在当地的合作社的房子里,这 我一直都没搞清楚,只是感觉他很孤独。他是这 个糟糕的队伍里最糟糕的一员,但却从未缺席过 训练,很明显他还因为自己的失误和三击不中出 局而沮丧。我曾经纳闷他到底为什么要来打球。 而且他还那么害羞,驼着背,长着痤疮,会被自 己的脚绊倒,会脸红,还有喃喃自语——真是个 经典。
他的母语不是英语,好像是亚美尼亚语或摩 拉维亚语之类的。总之是除了他们合作社的那对 老年夫妇,其他人都不会说的一种语言。他嘟囔 着在火星上凑合算是英文的东西,有时甚至还用 翻译盒,但基本上他都试图不去需要说话的场合。 然后,他还是错误不断。我们俩在场上肯定是出 尽了风头,我的身高只到他的腰间,我俩都像表 演魔术似的任由滚地球穿过我们。或者我们把球 截下来并追击,然后击球越过一垒手。我们很少 出局,这听起来很厉害,但其他人也都是这样。 在火星上,棒球是个容易得高分的运动。
不过总之是很美。像梦幻一般,真的。首先 是地平线,当你在一个像阿吉尔那样平坦的平原 上时,地平线只有不到5千米(3英里)那么远, 而不是10千米(6英里)。这对于地球人的眼睛 来说是非常明显的。他们场地的内场刚刚超过正 常尺寸,但外场必须是巨大的。在我的球队的场 地到死点是274.32米(900英尺),沿线是213.36 米(700英尺)。从本垒板上望去,外场围栏就像 地平线附近紫色天空下的一条绿线——我想告诉 你的是棒球场几乎覆盖了视野可见的整个世界。 好棒。
他们的场上有4名外场手,像垒球一样,球 员之间的球道很宽敞。可以这么说,这里空气稀 薄得和珠穆朗玛峰大本营一样,地面引力只是地 球上的0.38倍。所以当你实实在在地击中球时, 它飞得就像是被一根大球棒击中的高尔夫球一样。 即使在这么大的场地上,每场比赛都还有一些本 垒打。火星上很少有输家一个球也进不了的比赛。 至少在我去了那里之前是这样。
我是在爬上奥林匹斯火山之后去了那里,去 帮助他们建立一个新的土壤科学研究所。他们意 识到不能只通过看视频来尝试着做这个。起初我 利用非工作时间去攀登了腾瑞山区,但自从迷上 棒球之后,这爱好就占据了我大部分的空余时间。 好吧,其实是当他们问我要不要打球时我回答好 的。但我不做教练,我不喜欢对人指手画脚。
所以我就开始与大家一起用足球锻炼来热 身,活动一下我们那些永远不会派上用场的肌肉。 接着维尔纳开始打内场练习,格雷戈尔和我将开 始挥棒。我们像斗牛士似的。有时候我们会先把 球截住,然后狠狠地往一垒(有时是一垒手)的 位置击球。身高两米多、体型像坦克一样的一垒 手在接住击球后会和我们相互拍击对方的手套。 日复一日地如此练习后,格雷戈尔在我面前渐渐 地不像之前那么害羞了,尽管进步并不大。我注 意到他的扔球异常有力。他的手臂与我身高一样, 似乎无骨的样子,像是从鱿鱼身上扯下的什么东 西。他的手腕相当灵活,可以扔出厉害的高飞球。 当然有时候球在飞到一垒手头顶10米处仍然继续 上升,毫无疑问。我想,除了不必与周围人语言 交流之外,他打球也许是因为只有这样他才有机 会狠狠扔一件东西。我也注意到,与其说他害羞 还不如说是暴躁,或两者兼有。
不管怎样,我方的防守就是个笑话。安打 稍好一些。格雷戈尔学会了很有效地劈球和直击 滚地球中心。我也开始学着更好地掌握时机。我 有着多年垒球的缓慢投掷经验,挥棒练习又比 其他人晚开始了一周。所以在我开始游击手练习 之前,队员们肯定都认为他们多了个有缺陷的美 国队友。由于他们的规则限制,每队只能有两名 地球人,毫无疑问他们会对我的存在感到更加失 望。好在我渐渐地学会了掌握时机,那之后我打 得很好。问题是他们的投手没有突破性的进步。 这些大块头会照顾后方,并像格雷戈尔一样尽力 投球,但是他们的尽力而为却只能投出一个正 球。他们经常无意地将球直接朝你扔去,这挺吓 人的。但是如果他们把球速放缓,你要做的只是 注意抓住时机。
如果你打中了球,看它怎么飞吧!每次我成 功击球,那就像一个奇迹。你会感觉如果击打正 确,你就能将球放入轨道——事实上,“轨道”就 是他们对本垒打的昵称之一。注视着球离开场地飞往地平线时他们会说,哦,那是一个轨道。他 们有一个小铃铛,就像船上的铃铛,系在挡球网 上。每次有人打出一个轨道,他们就会在你绕场 跑的时候敲响那个铃铛。一个非常好的当地习俗。
所以,我很享受这项运动。即使在你大开杀 戒的时候,它依然是一个美丽的游戏。练球结束 后,我最酸痛的肌肉却是被剧烈大笑牵动的腹部。 我甚至开始在游击手的位置上获得了一些成功。 比如当我抓住飞到我右侧的球后,我会向反方向 迅速转身并把球扔向一垒或二垒。虽然自己感觉 很可笑,但还是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像一 个独眼龙在盲人国里的感觉——并不是说他们不 是很好的运动员,而是他们没有从小时候开始练 球,所以在直觉上有所欠缺。他们只是喜欢玩。 我看得出他们为什么喜欢这么玩——在紫色天空 下,黄绿色的球在辽阔无边的绿色场地上飞来飞 去,这很美丽。我们玩得很开心。
虽然我很早就起誓不做教练,但还是开始传 授格雷戈尔一些诀窍。我不喜欢告诉别人应该怎 么怎么样,指导这个运动太难了。但我向外场手 飞球的时候也很难不告诉他们应该在盯着球的同 时在下面追着跑,然后举手、抓球,而不是奔跑 的全过程都和自由女神像一样伸展着胳膊。或者 在他们轮流飞球(实际比看上去更难)时告诉他 们击球的技巧。热身训练时,格雷戈尔和我一直 在练习接球,他只是看着我的示范,并试图扔向 某个近距离的目标。他确实扔得很卖力,也取得 了进步,我看到他的投掷中有很多不同的动作。 他的投球会从各个方位出其不意地尾随着我,考 虑到他的手腕那么灵活,这也并不出奇。我必须 保持警惕,否则就可能接不住。他虽然控球不太 好,但很有潜力。
其实我们的投手是很糟糕的。他们挺可爱, 但哪怕你付钱给他们,他们也投不出一个正球。 通常他们每场比赛都会将10个或20个击球员送 上垒,就这还是五局一场的比赛。维尔纳会看着 托马斯把10个击球手送上垒才能安心地接手,然 后自己再送10个。有时候这样的情况会出现两 次。格雷戈尔和我会站在那里看着对方的跑垒者 走过,有时像游行的队伍,有时像杂货店前排队 的人群。当维尔纳进入投手垒包时,我会站在格 雷戈尔身旁说,格雷戈尔,你的手臂很好,你可 以比这些人投得更好。他会惊恐地看着我,嗫声 说不,不,不可能。
在一次热身赛中,他中断了一个非常巧妙 的曲线投球,但被我的手腕挡住了。接下球后我 走到他身边。“你有没有注意到球的运行曲线?” 我说。
“看到了,”他把头转向一边,“对不起。”
“不要说对不起,格雷戈尔,这就是所谓的曲 线球。它可以是一个很有用的投球手法。在球脱手 前的最后一刻猛地转动手腕,球会越过你的手飞射 出去。就像这样,看到了吗?来,再试一次。”
就这样我们开始了教授和练习。高三时我在 康涅狄格州队效力,这份荣誉大都来自刻苦笨拙 的投掷训练——曲线球、滑行球、指叉球,然后 转换。我看得出格雷戈尔只是碰巧才投出了那些 手法,但为了避免他感到迷惑,我让他只专注直 曲线。我告诉他,就像你第一次那样把球扔给我 就行。
“你不是说你不当我们的教练吗?”他说。
“我不是在教你!你就像那样扔就行了。在 比赛时候再扔得直一点,尽可能地直。”
他用摩拉维亚语对我嘟囔了几句,没有看着 我的眼睛。不过,他练习投直曲线球成功了。不 一会儿,他就完成了一个很漂亮的曲线。当然, 火星上的空气更薄,意味着球的阻力会很小。我 发现他们用的蓝点球比红点球的针脚更高,可他 们好像以为这没有什么区别,但其实是有影响的。 所以我把针脚磨平了,然后继续与格雷戈尔合作。
我们经常练球。我向他示范了如何绕臂投 球,想象着格雷戈尔的绕臂动作可能会把自己的 胳膊打成一个结。而在赛季中期之前,他就通过 绕臂投球扔出了一个很棒的曲线。我们没有把这 件事告诉任何人。他感到很兴奋,球瘾更重了。 我必须非常警惕才能抓住他的部分投掷,这也使 我在游击手的位置上发挥得更好。终于在一场依 然落后的比赛中,20∶0,击球手打出了惊人的高 飞球后我立即飞奔追赶,风带着球飞,我穷追不 舍。追到球之前我一直在这群吃惊的中场球员之 间来回穿梭。
“也许你应该打外场。”维尔纳说。
我说:“感谢上帝。”
从那之后我开始打左中心或右中心,我的场 上任务就是追赶飞向围栏的直球,然后扔给截球 员。或者更有可能我就在那儿站着,看着对手的 球员们保送上垒。当我开始像从前在场上那样唠 叨的时候却发现,在火星上打球根本没有人大声 嚷嚷,这感觉就像是在一个聋哑联盟里玩耍。我不 得不在两百码之外的中心场为整个队伍提供唠叨, 当然也包括对本垒板裁判的点名批评。虽然对本垒 板来说,我就像是个微型人,但我的表现仍然比他 们好,这一点他们也知道。很好玩。人们走路经过 时会说,嘿,那边一定有一个美国人。
有一次我们主场失利,比分好像是28∶121, 每个人都去吃东西了,格雷戈尔就站在原地望着 远方。我问他要不要一起去吃东西,他摇摇头。 他不得不回家工作。我也正要回去工作,所以我 俩一起走回城里,那地方就像德州北部的狭长地 带一样。我停在他的合作社外面,这是一个大房 子或者可以说是小公寓楼。我永远都分不清火星 上的哪儿和哪儿。他像个路灯柱似的站在那儿, 我正要离开的时候一个老妇人出来邀请我进去。 “格雷戈跟我提起过你。”她用很生硬的英语说。 他们把我介绍给他们厨房里的人,其中多数人的 个头都异常高大。格雷戈尔显出很尴尬的样子, 像是不希望我在那里,所以我尽快离开了。老妇 人有丈夫,他们像是格雷戈尔的祖父母。还有一 个和他年纪相仿的年轻女孩,像鹰一样看着我们 俩。格雷戈尔没有直视她的眼睛。
下一次训练时我问:“格雷戈尔,他们是你的 祖父母吗?”
“他们就和我的祖父母一样。”
“那个女孩是谁?”
没有答复。
“类似表妹?”
“是的。”
“格雷戈尔,你父母呢?他们在哪里?”
他只是耸耸肩,开始把球扔给我。
我印象中他的父母住在他们合作社位于另一 处的一个分社,但我不能确定。在火星上,我看到 很多我喜欢的事物——他们在合作社共同经营业务 的方式可以为他们减轻很大的压力,与我们在地球 上的生活比较,他们的日子相当悠闲自在。但我对 他们养育系统中的一些东西不是很懂——抚养孩子 的是团体、单亲或其他形式。如果你问我的话,我 认为这会造成问题。也许不管你怎么做,一群十几 岁的男孩准备猛揍某人的事都会发生。
总之,我们终于熬到了赛季的尽头,结束后 我打算返回地球。我们队的胜负纪录是3∶15,在 常规赛中排名最后。但他们为阿吉尔的所有球队 举办了最后的周末联赛。在这一连串的三局比赛 中还有很多要争取的东西。很快我们就打输了第 一场比赛,被归入输家类别中。然后,我们又打 输了下一场比赛,而且绝大部分的输球都是因为 我方失误,将对方保送上垒。维尔纳替换了托马 斯一会儿,当发现这样没有奏效的时候,托马斯 又回到了投手垒包上去重新替换了维尔纳。这一 幕发生时,我从中心一路猛跑到了垒包上对他俩 说:“伙计们,让格雷戈尔投吧。”
“格雷戈尔!”他俩都说,“没门!”
“他会比我们更糟。”维尔纳说。
“怎么可能?”我说,“你俩刚才连续十一次 让对方保送上垒。格雷戈尔要发生这么多失误的 话,天都黑了。”
他们同意了,但如你所料,当时他们很气 馁。我走向格雷戈尔对他说:“格雷戈尔,现在你 去试试。”
他非常抵触地说:“不,不,不,不,不, 不,不。”瞥了一眼观众席,有几百人,大多是朋 友和家人,还有一些好奇的路人。我看到里面还 有“像是”他的祖父母和他关系不明的女孩。格 雷戈尔越来越畏缩和苦闷了。
“来吧,格雷戈尔,”我说,同时把球放到他 的手心里,“听着,我会接住。就像热身赛一样, 你只要尽力扔你的曲线球就行了。”我把他拖到投 球垒包上。
维尔纳帮他热身时我走过去穿上了接球者的 装备,把一盒蓝点球移到裁判员的补给区前。看 得出格雷戈尔很紧张,我也是。我从未接过球, 他从未投过球,而场上已经是满垒,没有人出局。 这是一个不寻常的棒球时刻。
最后我准备就绪了,叮当作响着走向他。“不 用担心投掷太用力,”我说,“对准我的手套发曲线 球就行。直接忽略击球手。我会在每次投球前给你 信号,两个手指是曲线,一个手指是快球。”
“快球?”他问。
“就是让球飞得快一些。别担心,反正我们只扔曲线。”
“还说你不是教练。”他埋怨地说。
“我不是教练,”我说,“我只是要接球。”
我回到了本垒板后面就位。“注意曲线球,”
我对裁判员说。“曲线球?”他问。
比赛开始了。格雷戈尔像一只在祈祷的大 螳螂一样半蹲在投手垒包上,红着脸,但神情坚 定。他的第一个投球直接越过我们头顶打在了挡 球网上。两名球员在我去捡球的时候打进了球, 但是对方从一垒冲向三垒的跑垒者被我封杀出 局。我跑向格雷戈尔说:“好了,各垒现在都无 障碍,对准我的手套发球吧,就像上次一样,稍 微低一点。”
他把球朝着击球手扔去,击球手闪避了,球 直接飞入我的手套。裁判无语了。我转过身来给 他看我掌心的球。“是个正球。”我告诉他。
“正球!”他号叫着,咧嘴对我笑,“那不是 个曲线球吗?”
“当然是了。”
“嘿,”击球手问,“那是什么?”
“我们再给你演示一次。”我说。
随后,格雷戈尔把投球角度调低了。我一直 伸出两根手指向他示意,他就一直扔曲线球。这 些发球当然不可能都是正球,但也足够让他不至 于送太多击球手上垒。所有的球都是带蓝点的。 裁判员开始入迷了。
在两个击球手之间,我看到身后整个观众席 和所有的没有参赛的队伍都聚集在后挡板处观看 格雷戈尔的投球。火星上没有人见过曲线球,现 在他们拥挤在那里以获得最佳的视野,激动着, 喋喋不休地议论着每一个球的弧线。击球手会闪 避或虚晃一棒然后回头笑对人群,像是在说,看 到了吗?那是个曲线球!
我们找回了状态,赢了那场比赛。我们让格 雷戈尔继续投球,又赢下接下来的三场比赛。第 三场比赛中他扔了27个球,使9个击球手都因三 击不中而出局。鲍勃·费勒曾经在高中比赛中击 败了全部27个击球手,格雷戈尔就像那样。
观众看得起劲,格雷戈里的脸也不那么红 了,在投手区内也站得更直了。他仍然拒绝注视 我的手套之外的任何位置,但是他那坚定的恐怖 样子已经转变为惊人的集中力。他也许很瘦,但 他个子很高,在投手垒包上的他开始给人一种相 当强大的感觉。
所以我们又返回了胜利者的行列,接着进入 了半决赛。成群结队的观众在中场时找到格雷戈 尔,请他在他们的棒球上签名。大多数情况下他 看起来呆头呆脑的,但是有一次我看到他瞥了一 眼看台上他的合作社家人,微笑着对他们挥挥手。
“你的手臂感觉怎么样?”我问他。
“你什么意思?”他反问。
我说:“听着,这局我还想打外场。你能不能 投球给维尔纳?因为在接下来和我们比赛的队伍 中有几个美国人,欧尼和凯撒。我只是有预感, 他们也许能击中曲线球。”
格雷戈尔点了点头,这让我觉得只要有一个 手套让他瞄准了扔球,就再也没有什么事了。所以 我安排了维尔纳去接球,在半决赛时我又回到了右 中心区域。这场比赛是在灯光下进行的,球场就像 是暮光中紫色天空下的绿色天鹅绒。从中外场看 去,这一切都是那么渺小,像梦幻中的事物。
我的预感很准。我冲向欧尼的直球时使用了 滑垒来阻止它,然后我又跑了大概30秒穿过中心 场地,紧接着就遭到了来自凯撒的强大的德州式 围攻。格雷戈尔甚至在休息时过来祝贺我。
你知道那个有关“好球造就好打者”的老 话。在白天的比赛中我已经打得很好了,但现在 在半决赛中,我又打出了一个很高的快球。这个 击球很实在,以至于感觉像没有击中它就飞了起 来似的。飞越中外场围栏、飞入暮色的全垒打, 在球下落之前,我就看不见了。
在后面的决赛第一局中,我又复制了一个全 垒打,和托马斯背靠背——他向左,我还是向中 心。这是我的连续两次进球,我们要赢了。格雷 戈尔正在对他们进行扫荡。所以下一局上场时我 感觉良好,人们都在呼唤着再来一个全垒打。这 时我发现了对方投手那异常坚定的神情。那家伙 非常高大,不光像格雷戈尔一样高,也像很多火 星人一样有着强壮的胸肌。他向后跃起,然后把 他的第一个球笔直朝着我的头扔来。不是存心的, 但他失控了。然后我勉强把球击出界外,挥棒很 晚,摆动得很晚,回避着他内心的怒火,直到三 球两击。我对自己说,现在三击不中出局也不要 紧了,因为你已经击中了两个。
接着我听到格雷戈尔大声喊着:“教练,你行的!坚持住!保持警惕!”这 些鼓励都马马虎虎,算是在模仿我吧,其余队员都大笑起来。想必我以前曾经对 他们说过这些话。通常你在场上自然而然会说一些你自己都不以为意的话,我甚 至不能肯定他们是否曾听到我说这些话。但我绝对听到了格雷戈尔的话,在刺激 着我。回到了投手区,我想我根本不喜欢当教练,我在游击手位置上打了10场 比赛都试图不去教你们。我很恼火,几乎在没有注意到投球的情况下就把球击出 右边围栏,甚至比我的前两球更高更远。膝盖高的快球,内角。后来欧尼对我 说:“你搞定了那个小宝贝。”我的队友围绕各垒敲响了小铃铛,在三垒到本垒的 沿途我大笑着和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击掌。之后我坐在长凳上,摸着被飞球撞疼的 手,还能感觉到球在飞。
最后一局比赛我们领先,4∶0,而对手球队决心要赶上我们。后来格雷戈尔 累了,他送了几个击球员上垒,然后悬投(曲线球)失效,被对方的大个子投手 狠狠一击,高高地飞过我的头顶。虽说现在我追赶直球表现不错,可一旦球飞到 头顶我就不知所措了。所以转身开始朝围栏跑去,想着要么它飞出界,要么打在 围栏上被我捡到,只要它不在我头顶就好。在火星上跑步太诡异了。一会儿你跑 得飞快,一会儿你就得原地旋转以防脸部着地。当看到警告的轨迹时我正是这么 做的,回头看到球正要落下时,我就跳了起来,试图笔直跳起。当时,我的冲力 很大而且我彻底忘记了引力的问题,所以我直射出去抓住了球,很惊人,但随即 发现自己正在围栏上飞行。
我下落后在沙尘中打着滚,球紧紧地握在手中。我再次越过围栏举起球以 示我拿到了。但是他们还是给对方投手记了一个全垒打,因为根据当地的规则, 抓住球的时候你必须人还在场内。这我并不在乎,游戏最重要的就是让你去遵守 那些规则。那个投手因此而得分也很好。
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格雷戈尔痛击了对手,我们赢了比赛。我们被热烈的 人群蜂拥围堵,尤其是场上英雄——格雷戈尔。每个人都希望能得到他的签名。 他没有说什么,但也没有驼着背,只是看起来很惊讶。随后维尔纳拿出两个球, 每个队友都签了名,算是作为格雷戈尔和我的奖杯。后来我发现奖杯上有一半名 字是玩笑,类似本垒打之王“米奇·曼托”等名字。格雷戈尔在上面写着,“嗨, 阿诺德教练,来自格雷格的问候”。这个球至今仍放在我家的写字台上。
Copyright © 2000 by Kim Stanley Robinson,
Copyright licensed by The Lotts Agency Ltd.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作者简介
金·斯坦利·罗宾逊(Kim Stanley Robinson):美国著名科幻作家,著有作品《黑色空气》 《盲几何学家》《火星》三部曲等。作品曾多次获得雨果奖、星云奖和轨迹奖等重要奖项。
译者简介
李光辉,中国文化研究院(香港)编辑部英文编辑,大型中国文化教育公益网站《灿 烂的中国文明》英文版翻译项目负责人、译者、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