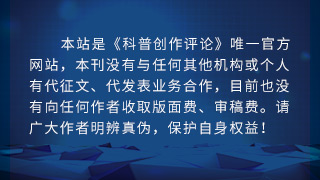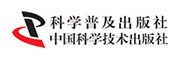他者之眼:吴明益《复眼人》和异样观看的挑战
《科普创作》
[美]罗鹏 著 王丁丁 译
2020-06-22 13:32
我常自问,只为看清我是谁,以及当我被动物的凝视(如猫的目光)攫住时,我是(在跟随)谁——彼时我赤身裸体而万籁俱寂,我遇到了麻烦,是的,我难以克服自身的窘困。
——雅克·德里达,《动物故我在》[1]3
在吴明益2011年的小说《复眼人》中, 一个名叫阿莉思的台湾女人独自生活在台湾 东海岸。[2]阿莉思的家有一个充满爱意的名 字——“海边住宅”,由她的丹麦丈夫杰克 森建造。夫妻二人和儿子托托在这里生活了 很多年。杰克森和托托神秘失踪后,阿莉思 开始有自杀倾向,甚至已经下定决心结束自 己的生命。因此,当突然有地震时,她满怀 期待地迎接地震后的潮水猛涨,“又想起自己 本来就想寻死,不禁苦笑起来”[2]50。
然而,当阿莉思向窗外望去,恰巧看到 一只颤抖的小动物趴在一块浮木上漂过,她 竟突然重新萌生了生存意志:“好像是一只小猫。不,不是好像,确实是一只小猫。小 猫正以忧伤之眼望向她。”[2]51阿莉思救下小 猫,并给它取名为Ohiyo(日语“早上好” 的意思)。她注意到的第一件事:“非常特别 的是,小猫一只眼是蓝色的,另一只眼是棕 色的。”[2]51后来,当另一个人问她:“两只 眼睛不一样的颜色,看到的世界会一样吗?” 阿莉思反问:“有人两只眼睛看到的是一样的 东西吗?”[2]64

图1《复眼人》(新星出版社,2013年3月)
尽管吴明益的小说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两 个问题,但我们却能从一种光学现象中得到 答案。当人用一只眼睛看静止图像,用另一 只眼睛看移动的物体时,静止物体就会从视 野中消失。这种现象被称为柴郡猫现象—— 以那只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的 《爱丽丝漫游奇境记》(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中著名的猫科动物命名,它能够 让自己消失,只留下露齿的笑容——这种错 视是由双眼竞争造成的,人们通过双眼看到 的场景如此不同,以至于大脑无法协调。换 句话说,吴明益笔下阿莉思提出的问题的答 案是:我们不能。我们两只眼睛所感知的东 西总是不同的,有时候这两种视角甚至会公 然发生冲突。
尽管吴明益写小说时,不太可能联想 到这种错视现象,不过在为主人公取名“阿 莉思”时,他受卡罗尔的《爱丽丝漫游 奇境记》及其续集《爱丽丝镜中奇遇记》 (Through the Looking-glass and What Alice Found There)中主人公名字的启发。至今, 卡罗尔的书在东亚依然大受欢迎,例如, 2017年10月,在首尔举办的名为“跳进兔 子洞”的大型多媒体展览,随后在台北和其 他东亚城市巡展,两年内吸引了数十万名参 观者。[3]正如这次展览戏剧化呈现的内容, 卡罗尔的书运用了一种幻想的,甚至超现实 的叙事手法,创造出一个儿童的世界——以 及与之对应的世界观——它与典型的成年人 世界截然不同,以至于许多读者很难将书中 的世界观与他们自己的世界观联系起来。
如果吴明益与卡罗尔二人书中同名的主 人公之间,仅仅存在隐秘的联系,那么法 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在其1997年的著作《动物故我在》(TheAnimal That Therefore I Am)中,则直接提 到了卡罗尔的书。德里达以讨论自己被猫咪 看到裸体时的反应开篇:
在盯着我的猫面前,我是否应该作为一 只不再具有赤裸感的动物而羞愧,还是应该 作为一个仍然保持赤裸感的人而羞愧?那么 我是谁?我之所是(追随)的是谁?应该向 谁提出这个问题——如果不是向他者,或许 是向那只猫?
我必须首先澄清,我所讨论的猫是一只 真正的猫,真的,相信我,那是一只小猫, 而非一只猫的形象。[1]5-6
接着,德里达讨论了一系列哲学和文学 作品中提及的猫,随后对卡罗尔的书提出更 详尽的思考:
“我的”猫咪(但从不是一只属于谁的 猫)并不是在《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中说话 的那只……
时间不允许,否则我当然愿意将我的全 部讲话都放在对卡罗尔的解读上。[1]7
尽管柴郡猫是卡罗尔作品中最具代表性 的猫,但德里达更感兴趣的是卡罗尔对爱丽 丝自己养的小猫的描述——尤其是爱丽丝的 想法,她觉得不可能和小猫对话,因为“它 们总是说同样的东西”。或者,正如德里达 所说,“你能跟一个动物说话,对前面所说的 真正的猫说话,因为它是一只动物,但是它 不回答,不真正地回答,从来如此,这就是 爱丽丝得出的结论”[1]8。相应地,德里达对 照着谈及爱丽丝的小猫和他自己的猫,他实 际上是在发问:如果面对一个极端他者,与 之可能没有任何共同的视角,不能形成任何 有意义的对话,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吴明益的《复眼人》同样关注视觉问 题,以及如何与世界观截然不同的他者交流。这部小说由几个交织的不同的叙事线索 组成,登场人物从中国台湾地区原住民到欧 洲环保主义者。其中最有趣的情节之一,围 绕一个名叫阿特烈的年轻人展开,他来自一 座名叫瓦忧瓦忧的太平洋小岛。岛上的瓦忧 瓦忧族是一个与世隔绝的部落,与其他社群 几乎没有任何联系,直到一系列离奇的事件 发生,阿特烈与阿莉思不期而遇。本文将讲 述阿莉思和阿特烈之间的互动及其提出的更 广泛的环境问题和本体论问题。
一、垃圾
吴明益小说中的瓦忧瓦忧族有一个由来 已久的习俗,除非一个家庭的长子夭亡,否 则次子“出生后第一百八十次月圆时”[2]11, 必须用草和泥建造一艘小船(称为“泰拉瓦 卡”),然后带足十天的食物出海。离开小 岛后,次子不能回头,因此,人们认为他们 必死无疑。而主人公阿特烈有一个双胞胎兄 弟,比他早出生几秒钟,但阿特烈仍然是次 子,在他十五岁生日后,不得不踏上“不归 路”。于是,他为自己建造了一艘“泰拉瓦 卡”,划向大海。离开小岛的第七天,储备 的食物已经耗尽,并且,阿特烈发现“泰拉 瓦卡”开始渗水。他拼命地想挽救它,但船 最终还是沉了。这时,他只能在广阔的海域 游泳,最终体力不支,陷入昏迷。醒来时, 他发现自己来到了一座漂浮的小岛,小岛是 由“各种颜色混合的奇怪东西组成的”[2]26。 他开始着手探索这座岛,并制作了各种可能 用得上的物件——收集雨水的塑料袋、制作 衣服的布料和搭建临时避难所的防水帆布。 他还发现了一些“书”和“棒子”,为了打 发时间,他开始“阅读”书籍,还用“棒子”在自己的身上刻画精致的图案。
阿特烈在垃圾岛上的生活,既辛酸又 超现实。遥远的工业化社会丢弃的漂浮垃圾 岛,出乎意料地救了他。他此前从未接触过 这些垃圾,它们却短暂地成了阿特烈的全部 世界,同时又好像架起了一座桥梁,使他从 瓦忧瓦忧步入了工业发达的中国台湾地区。 在一场末日般的冰雹风暴中,这座垃圾岛被 海啸卷到了台湾东海岸。接着,风暴席卷了 阿莉思的“海边住宅”,导致附近的海滩上 “堆满了各式各样特异的物品,令人误以为 自己正登上一个远方的星球”[2]121。
垃圾岛在台湾东海岸搁浅后,吸引了大 量访客,包括试图清理垃圾的当地人、有兴 趣研究这些垃圾的科学家、记者和其他围观 群众:
这个星期以来,海滩上聚集了各种专 家,有洋流学家、潮间带生物学家、塑化 物学家……今天还有一队从德国来的垃圾专 家,据说是专程来“研究”我们分类好的垃 圾。因此这些刻意被留下来的样本要把寻得 地点、重量都标示得清清楚楚,用标签贴上 去。听说那位垃圾专家曾写过一本书,从德 国鲁尔工业区的一处掩埋场来讨论德国的文 化史,所以他也建议,应该把这些垃圾以 “功能性”来区分,而不是以回收价值来区 分,因为这些垃圾恐怕是未来世界文化史的 重要材料。[2]166
公众和科学界对小说中垃圾堆积的关 注,映射了吴明益作品中垃圾主题的展开。 除了提醒人们关注他们常常忽视的工业社 会,小说此举还引领读者拓展了对自己和社 会的理解。
从这一方面来说,小说所描写的垃圾 岛,与中国当代文学电影对垃圾处理问题的广泛关注产生共鸣。许多作品结合虚构和非 虚构手法,试图引起人们关注当代社会处理 垃圾的方式,以及社会如何将垃圾处理过程 置于公众视线之外。例如,2011年,即《复 眼人》出版的同一年,中国摄影师王久良的 纪录片《垃圾围城》上映。拍摄这部纪录片 的起因是王久良对北京垃圾收集车将城市垃 圾运往何处的好奇。因此,王久良骑着摩托 车跟踪其中的一些卡车,发现大多数卡车的 目的地是城市外围的一些露天垃圾场。在接 下来的两年里,王久良在这些露天垃圾场进 行调查,并利用卫星图像定位。除了记录这 些垃圾场本身,王久良同样关注那些在垃圾 场内部和周边谋生的人,其中许多人靠在垃 圾堆里搜寻仍有利用价值的物品来生活。
之后一年,郝景芳发表了中篇小说《北 京折叠》,从科幻小说的视角审视北京。这 部中篇小说的背景设定在未来,北京城市规 划者实施一项彻底改造北京城市空间计划之 后的几十年。更具体地说,规划者根据城市 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将其分为三类,并重 新设计城市形态,使其自我折叠,为这三个 阶层创造各不相同的城市空间。故事围绕第 三空间的一名垃圾收集工展开,他属于被 “塞到夜里”的那群人。
像郝景芳从被“塞到夜里”的视角描绘 了一个反乌托邦的未来北京一样,另一位常 居北京的作家陈楸帆,在他2013年出版的 首部长篇小说《荒潮》中也采用了类似的视 角。像《北京折叠》一样,《荒潮》的背景 设定在未来某个时期的一座都市,原型为汕 头市(作者家乡)贵屿镇。在陈楸帆的小说 中,城市名为贵屿的同音词硅屿,暗含其作 为主要电子垃圾回收地的地位。陈楸帆的小 说侧重描写大批外来打工者,他们从事着硅屿电子垃圾处理行业中肮脏且危险的工作, 主角是一个名叫小米的年轻人。故事中,她 遭到了当地男性的强暴,之后意识分裂—— 她的原始意识“小米0”和另一个控制论的 意识“小米1”。小米的原始意识感知到第二 意识的存在,对她既敬畏又恐惧。最后,小 米将两个主体合二为一,每个主体对自身及 其所存在的世界都有独特的理解。
上文提到的三部作品均反映了中国现代 都市中垃圾的状况,它们也对人们如何看 待垃圾本身——和垃圾如何看待人类——做 了更广泛的评述。在法国精神分析学家雅 克·拉康(Jacques Lacan)的《研讨班11》 (Le SéminaireⅪ)的著名段落中,他富有 争议性地提出我们如何通过垃圾看待自己 这个潜在问题。拉康在文中回忆道,在他 年轻时的一次钓鱼旅行中,同伴指着船边 一个空沙丁鱼罐头大声说:“你看见那个罐 头了吗?你看见它了吗?好吧,它看不见 你!”[4]拉康回想起这一观察使他醍醐灌顶, 因为经过一番思索后他意识到,如果说罐子 “看不见”他,那就意味着他仍然处于罐子 的抽象视域内:“从某种意义上说,罐子一 直在看着我。它在光点的层面上看我,所有 看我的东西都被安置在这个光点上。”拉康 补充说:“我不是在用比喻的说法。”[4]
在《复眼人》中,垃圾岛撞上台湾东海 岸,不仅戏剧性地加剧了人类与自然世界之 间的紧张关系,还引发了人们对何为人类这 一问题更深层的思考。小说开头对阿特烈在 他人丢弃的垃圾筑造的浮岛上艰难维持生活 进行了描写,之后则有一段描写莎拉——一 名来到台湾调查垃圾并协助清理的国外环保 人士——和当地原住民达赫的讨论。达赫解 释他们如何分拣处理垃圾,随后莎拉询问当地居民的情况,达赫回答说:
有不少是Pangcah(邦查),这里的阿 美人自己称自己为邦查,他们多半都投入复 原的工作。我很怕这片海岸完了,渔场也完 了,邦查的海洋文化也毁掉了一部分。对于 汉人来说,海的污染就是没有钱而已,但对 于邦查来说,海是他们的祖先,太多神话是 跟海相关的,没有祖先,还当什么人?
接着,莎拉问达赫是不是邦查,他回 答:“不,我是布农……Bunun的意思,是真 正的‘人’。”[2]219
二、岛屿
《复眼人》开篇告诉我们,“瓦忧瓦忧 岛民以为世界就是一个岛”,他们将它比作 “大水盆里放了个小小的空蚌壳”[2]7,小到早 餐之后、午餐之前就可以绕着走完一圈。瓦 忧瓦忧既代表岛民经验的物理视野,也展现 了他们全部的宇宙观。具体来说,岛民形成 了一种与环境考量密切相关的世界观,尤其 是维持人类与非人类范围之间健康平衡的重 要性。
例如,瓦忧瓦忧人相信他们的祖先最初 生活在广阔的海域,但后来“不断繁衍、任 意取食、狂建城市、毫无节制,几乎把附近 的水族赶尽杀绝”[2]151。为了应对这场危机, 他们的神——卡邦——降下一系列自然灾难, 几乎使整个种族灭绝。然而,在最后一刻, 卡邦怜悯瓦忧瓦忧人,决定再给他们一次机 会——但必须满足他一个条件:
我可以允诺你们一个岛,但你们的族 人人数不得超过岛上的树,且你们将失去在 水中长期生活的能力,失去广大无边自由的 海,你们将体会被海所囚禁的孤独,饱尝溺死的恐惧。海将从盟友变成杀戮者,供给者 变成仇敌,但你们仍得依赖它、信任它、崇 拜它。[2]151
因此,岛上颁布禁令,人口绝对不能超 过树木数量。除此之外,还有一项补充规定: “由于岛可以生养的地方有限,一个家庭只 能拥有一个男丁,次子必须在满一百八十次 月圆的年纪时,单独乘‘泰拉瓦卡’出海, 永不回头,即使掌海师与掌地师的子嗣也一 样。”[2]154这个传说不仅解释了瓦忧瓦忧人 的起源,还将岛屿化为地球的缩影。也就是 说,瓦忧瓦忧岛和地球一样资源有限,容易 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卡邦的法令规定每个 家庭的次子必须在十五周岁时离开岛屿,象 征着社会必须与自然环境保持平衡。
考虑到阿特烈来自一个相信岛屿就是 全世界的民族,离开瓦忧瓦忧岛之后,他最 终被困在另一个岛上实在再合适不过:一个 漂浮在公海上的垃圾岛。后者的灵感来源于 “太平洋垃圾带”现象。它出现在北太平洋 环流,是世界五大垃圾带之一。当人类生产 的垃圾残骸漂流到大型循环洋流中心相对静 止的水面时,就形成了太平洋垃圾带。它由 成千上万吨人造物构成,主要是不可生物降 解的塑料。由于大多数微粒十分微小,还有 部分淹没在水下——分散在150多万平方千 米的区域内——一般情况下很难被观测到, 其真实性仍在调查中。但在吴明益的小说 中,垃圾堆积得如此繁密,以至于阿特烈可 以在上面站立行走。真实的太平洋垃圾带和 虚构垃圾岛之间的另一个区别在于,前者在 北太平洋上相对静止,而后者离开了它最初 的位置,正缓慢地向西移动。阿特烈在这座 浮岛上生活,直到抵达了台湾东海岸。
一边是瓦忧瓦忧人试图维持人与自然和谐平衡,一边的垃圾岛则体现了人类维持平 衡过程中普遍失败的症候。在某种程度上, 台湾是这两种趋势的结合体。吴明益自小说 开篇就强调,台湾面对人类活动引起的气候 变化时的脆弱性。如阿莉思丈夫在台湾东海 岸附近修建的“海边住宅”,正日益受到潮 水上涨的威胁。地震和随之而来的风暴潮打 断了阿莉思的自杀企图,而那只是海平面上 升的一个极具戏剧性的表现。就像海啸把垃 圾岛倾倒在台湾东海岸,也捕捉了更广泛的 环境剧变过程的缩影。
地震后的潮涨和随后到来的海啸,不仅 威胁和重组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 系,也将两种与阿莉思视角截然不同的存在 带到她面前。首先,如前所述,涨潮为她带 来小猫Ohiyo,重新点燃了有自杀倾向的阿 莉思的生存意志。其次,海啸带来的垃圾岛 席卷海岸线,也带来了随它漂过太平洋、艰 难求生的阿特烈。海啸过后的第二天,阿莉 思出门散步,发现阿特烈被困在一棵倾倒的 树下,他的腿骨已经粉碎。阿莉思救下阿特 烈,并照顾他恢复健康,在此期间,他们尝 试教对方各自的语言。阿莉思把小猫当作她 失踪的丈夫和儿子的替代品,类似地,她也 把阿特烈当作她生活中这两个缺席人物的替 代品。在照顾阿特烈的过程中,阿莉思甚至 一直将他的存在对外保密。阿特烈之前的 生活一直在偏远的岛屿上,与外界文明没 有任何接触,她担心他接触台湾社会后会 造成过度创伤。所以大部分时间,只有他们 二人待在一起,努力嫁接起各自以岛屿为基 础的世界观。
吴明益的小说借瓦忧瓦忧岛、垃圾岛和 台湾岛,戏剧化地呈现出一系列全球环境问 题,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可以将地球看作一座漂浮在宇宙中的孤岛。1968年平安夜, “阿波罗8号”上的宇航员拍摄了一张后来 被称为“地出”(Earthrise)的经典照片。这 是一张在月球轨道上拍摄的彩色照片——前 景是毫无生气的月球表面,远处可以看见彩 色的地球——现在,人们广泛承认这张照片 促进了全球环境运动的兴起。尽管“阿波罗 8号”上的宇航员不可能预料到这张照片最 终带来的影响,但他们所见证的画面不会泯 灭。正如指挥舱宇航员吉姆·洛弗尔在照片 拍摄后不久所说:“从这里看去,地球是浩瀚 太空中一片巨大的绿洲。”
与此同时,吴明益小说对岛屿的讨论, 也针对地球仪和感知整个地球的含义作了相 似的反思。例如,阿莉思与阿特烈聊天时, 她吹鼓了之前为儿子托托买的充气地球仪:
你看这个球,这就叫地球,我们住的星 球,不,不是我的,是你跟我的,你看,我们 住的地方就像天上的星星,只是我们住的这个 星星叫作地球。这个球是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地 球的模型,我买给我儿子的,晚上会发亮呢, 因为上面涂了一层夜光的涂剂。这个世界上有 的东西会发光有的不会,有的像月亮有的像太 阳。你怎么叫那个?那露沙?太阳呢?另外一 个,白天出现的那个?伊瓜沙?[2]160-161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即使阿莉思试图用 地球仪与阿特烈分享她对地球的认识,她也 承认,阿特烈对世界的理解根植在不同的词 汇和与之对应的概念框架中。
三、视觉
小说开篇,阿特烈的“泰拉瓦卡”沉 没,他在开阔的海面游泳时晕了过去。他恢 复意识后,回想起梦中设法抵达一座岛屿,岸边站立着“一群少年,他们眼神忧郁,在 应该是手的地方长出鳍来,全身斑驳,像在 礁石上打滚一辈子”[2]25。阿特烈在垃圾岛度 过的第一个夜晚,他遇到了这样一群鬼魂, 他们解释自己是之前死在海上的次子们的幽 魂。他们承认一直跟随阿特烈的“泰拉瓦 卡”直到它沉没,但又补充说他们无力帮助 他,因为他们“必须遵守不施援手也不刻意 毁灭”[2]28。
另外,在小说接近尾声处四个系列小节 中,姗姗来迟地讲述了阿莉思丈夫杰克森死 亡的情节,同时介绍了与小说标题同名的神 秘人物:复眼人。杰克森搬到台湾之后,便 迷上了登山运动,有一天晚上,他决定在黑 暗中“盲攀”陡峭的悬崖,不使用任何辅助 设备。然而,在下降到一半的时候,他失去 抓地力,摔下悬崖。他掉在下方的岩石地面 上,惊奇地发现自己还有意识,但是感觉身 体里每块骨头都已经粉碎。这时神秘的复眼 人出现了,眼睛像昆虫的眼睛:
不过整体来说,男子的眼和头部比较起 来,并没有比一般人大,但复眼极小,那复 眼上头的单眼少说也有几万枚,每枚单眼如 此微小,微小到肉眼几乎无法确定它的存在。 那自己又怎么确定看到了那样的景象呢?[2]254
就像在阿特烈濒死时造访他的幽灵一 样,这个复眼人被描绘成人与动物的复合 体,人在生与死的边缘才会看见。此外,就 像次子的幽灵一样,复眼人处于一种纯粹观 察者的位置,或者用他的话说:“只能观看无 法介入,就是存在的唯一理由。”[2]257
换句话说,次子幽灵和复眼人都象征 着凝视的具现,这种凝视包含——同时超 越——人类的视觉。就像拉康的沙丁鱼罐 头,这些观察者挑战我们,让我们不再把人类想象为凝视(以及伴随着的价值选择)的 唯一拥有者,而是把人类看作根植于(非人 类)世界的更广阔世界观中的形象。
从非人类视角看自己和世界意味着什 么?这些问题位于两种密切相关的理论范式 核心,这两种范式在环境和本体论讨论中逐 渐得到广泛认同。首先,阿恩·内斯(Arne Næss)于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了深层生态 学(deep ecology)概念,提倡一种处理环 境和环保主义的方法,避免突出强调人类中 心主义。也就是说,一些环境话语主张,保 护环境是为了维持人类的生活质量,而深层 生态论者则主张保护环境是为了所有生命。 再看更近的时代,过去的几十年中,诞生 了所谓的“物导向本体论”(object-oriented ontology)的哲学研究分支,提倡进一步推进 深层生态学的反人类中心主义,并尝试构想 一种不仅独立于人类,甚至独立于生命本身 存在的世界观的意义。正如继格雷厄姆·哈 曼(Graham Harman)所说:“这个世界,并 不是那个对于人类来说显而易见的世界;思 考一种超越我们思维的现实并非无稽之谈, 而是使命所在。”[5]
虽然吴明益在《复眼人》中没有明确提 及深层生态学和物导向本体论,故事叙事也 以人类为中心,但它在很多地方促使读者思 考,如果不依赖一套以人类为中心的假设看 待世界意味着什么。除上述例子外,体现这 种趋势最明显的情节,也许是阿莉思和她丈 夫杰克森就台湾如何受到气候影响展开的一 系列辩论。阿莉思注意到,有些人对灾难性 洪水的反应也许是“把灾难拟人化,说大自 然‘残酷’‘不仁’,随口囔囔而已”[2]48,杰 克森这样回应:
其实自然并不残酷。至少没有对人类特别残酷。自然也不反扑,因为没有意志的东 西是不会“反扑”的。自然只是在做它应该 做的事而已。海要上升就上升吧,我们到时 候搬家就行了。来不及搬家顶多就死在海里, 变成鱼的食物。这样想不是也不错吗?[2]48
作者简介
罗鹏(Carlos Rojas),美国人,杜克大学亚 洲与中东研究系教授,昆山杜克大学人文研究中 心联合负责人。研究领域包括中国近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性别研究、视觉影像艺术、批 判理论等,著有《裸视:关于中国现代性的反 思》(The Naked Gaze: Reflections on Chinese Modernity)、《长城:文化史》(The Great Wall: A Cultural History)、《离乡病:现代中国的文化、 疾病,以及国家改造》(Homesickness: Culture, Contagion, and National Transformation in Modern China)等。余华和阎连科作品的重要 英文译者,译有《兄弟》《受活》《四书》《炸裂 志》《耙楼天歌》等。
参考文献
[1] Jacques Derrida. The Animal That Therefore I Am. Edited by Marie-Louise Mallet[M]. New York:Fordham University Press,2008.
[2] 吴明益 . 复眼人 [M]. 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
[3] 台湾展览官网 . 跳进兔子洞:爱丽丝梦游奇境体验展 [EB/OL]. [2020-04-05]. http://www.justlive.com.tw/alice/.
[4] Jacques Lacan. The Four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Psychoanalysis[M]. Edited by Jacques-Alain Miller. Translated by Alan Sheridan. New York:W. W. Norton & Company,2005.
[5] Graham Harman. On the Undermining of Objects:Grant,Bruno, and Radical Philosophy[M]//Levi Bryant,Nick Srnicek,Graham Harman. The Speculative Turn:Continental Materialism and Realism. Melbourne:re. press,201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