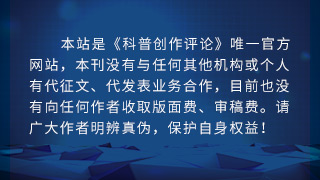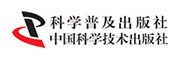弗兰肯斯坦怪物的银幕显影
——西方后人类科幻电影中身体话语的哲学溯源和文化论争
科普创作评论
林伟
2024-11-12 11:01
凯瑟琳·海勒(N.Katherine Hayles,又译海耶斯)认为,后人类主义已不再是遥远的地平线的云彩,而是迅速地迫近日常现实[1]26-27。诚如所言,随着科技的发展,器官移植、人机分离、虚拟身体等科幻概念日渐进入人们的生活中,人机合体的赛博格成为可预见的未来。“后人类”意味着现代生命科学和医疗技术对身体和思维的干预不断加深,使传统意义上的物种和文化疆界变得模糊。西方自由人文主义(liberal humanism)对“人”的定义面临崩塌。自20世纪60年代“赛博格”的概念被提出后,科幻电影中出现了丰富多彩的后人类身体想象。科幻文化中的赛博格形象可追溯到玛丽·雪莱(Mary Shelley)的《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小说首次探讨了借助医学技术创造出有机生命体的主题。在今天的科幻作品中,赛博格被用来泛指兼具人类和机器特征、人机混合的生物性存在。科幻小说、电影、游戏等各类流行文化实践中描绘了人类借助基因改造、机械义肢和克隆技术,以超越身体极限的主题,其中人机融合、互动的想象更引发了关于后人类身份的探讨。
科幻世界是现实社会的心理外延。后人类语境下的身体建构是科幻文艺作品重要的主题之一,是对人类生命形态的终极哲学追问。后人类科幻电影作为一种流行文化叙事类型,为理解科技的演变规律和发展趋势提供了一扇窗口。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认为,批判知识要有效地干预社会结构,就必须以某种叙事模式,通过间接的陌生化,让人们反思自身的绝对局限性[2]。在当下流行文化叙事中,后人类身体想象构成了一个充满矛盾、斗争和协商的场域,随着科技的进步,生物科学、医学技术不仅刺穿了人类的身体,也侵入了人的思维,自然身体的技术化、物种界限的模糊带来了“人的终结”的论调。后人类科幻中的身体叙事一方面允诺着技术与自然生命融合带来的乌托邦愿景,而另一方面,被技术侵染后的怪诞、失控的身体意象也折射出对启蒙人性丧失的恐惧。
一、后人类身体的哲学溯源
自17世纪以来,笛卡尔(René Descartes)开创的身心分离学说一直是西方文化主体建构的核心思想。身心二元论认为“思维/灵魂”在人的主体建构中占绝对支配性。代表着生物性的身体与象征着超验性的意识被对立起来,意识具有自主选择的能动性(agency),对主体的生成起着关键作用。西方现代哲学将身体与精神剥离开来,将精神凌驾于身体之上:“我们用不着肉体就领会它(精神)存在,而且我们可以否定任何属于肉体的东西属于精神。”[3]身体作为精神/灵魂的临时居所,堪比上帝制造出的机器。人体器官的运作犹如机器的运转。人的核心属性被定义为“精神存在”,与身体所象征的“生物存在”相对立。理性与抽象特性赋予人类精神世界以超验性,使得身体进入了漫漫长夜。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奠定了西方自由人文主义思想的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身心二元论将人类精神置于宇宙中心的同时,实际上也默许人类对自然世界进行征服和开拓。由于启蒙传统中与思维对应的身体概念与“白人/男性/基督徒”形象密切关联,而性别与种族的他者则被放逐于“自然世界”,与超验性意识所主导的“文化世界”形成对照。身心分离传统的身体观确立了无标记的白人男性身体的核心位置,而他者的身体被编码到人类身份之外[4]。
而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在赛博格身体中发现了一种解放性潜力,人机融合的赛博格具有一种可塑性和流动性(fluidity),使得传统意义上的生物学疆界变得模糊,从而挑战了自由人文主义身体观中的性别、种族预设[5]153-154。在后人类语境下,生物科学不断入侵人的思维和身体,自然身体的技术化使身心二元论中“纯洁”的人类主体性无法立足。如果说后现代理论的哲学追问,揭开了主客体二元对立中隐含的权力机制,那么后人类境遇更是将人们引向一种主客体关系的纠结:人越是希望与客体划清界限,就越会与客体更加紧密地纠缠在一起。后人类医学技术挑战了人们对身体、自我和他者的界定。器官移植正是因为模糊了自然与机器的边界,因而引发了大众对医疗技术的抵触情绪。赛博格是医学技术对身体改造的终极体现,因此挑战着自由人文主义核心的二元对立——思维与身体、人与非人、自然与人工。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后人类思想论争中,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思维模式——超人类主义(transhumanism)和批判后人类主义(critical posthumanism)。超人类主义延续了笛卡尔身心二元论的思想传统,肯定人的精神的超验性,并在赛博格身体中看到了新的自由主体潜能,即借助科技手段延续、拓展“自我”的能动性和意志,实现人对自我的超越。而批判后人类主义则认为人类的知识、行为体系都是一种社会构造,如福柯所言,人“不过是个近代的发明”[6],终将被其他的理念和社会建构所代替。海勒、哈拉维等思想家都对启蒙理性中的人类中心主义思维发起了挑战,认为自由人文主义的身体观是西方狭隘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表现。因而,批判后人类主义表现出一种去中心化的文化诉求,要求重新审视“人”的主体性。而赛博格身体中蕴含着一种解放性潜能——不是借助技术继承、发扬超验的“人类”精神,把人从脆弱的肉身中解放出来,而是将身体从人类中心主义思维模式中解放出来,“在我们当下的技术媒介社会中寻找一种新的、替代性的政治、伦理能动性”[7]。
二、从身体机械论、后人类医学到超人类主义
自工业革命以来,机械隐喻广泛地存在于西方文化的身体话语中。“身体被视作引擎、电器或管道系统,用机械的语言来形容身体内部的工作机制。”[8]8920世纪末的计算机技术飞跃更是使身体被想象为一个电脑系统。哈拉维就此指出,计算机身体隐喻使得人体被视为半机械化的,以至于疾病也被视作一种“通讯故障或通讯病”[8]89。身体机械论契合了身心二元论对精神的超验性和身体的物质化的对立区分,人体被认为是由无数微小的可替换的部件组成的,如果有“部件”损坏,就可以通过机械技术进行修复和改良。这种思维在后人类技术语境下得到了进一步体现:“技术之于生物医学的重要性无异于‘用机械来修复机械’……在高新技术医学中,器官移植和人造器官的使用,如起搏器、人工关节和助听器等,一方面受到这种意象的支持,一方面又加强了这种意象”[8]88-89。赛博格的核心理念正是医学技术/机器对身体的直接介入,而当下的医学也正是生物学、化学、药理学、电脑工程甚至纳米技术的交叉[9]114。
因此,后人类语境下,人的本质被视为一种技术性存在,而并非仅仅是生物性存在,因此,未来人类的演变实际上是与技术并行的。后人类医学通过对身体的改良,来打破传统意义上“人”的局限。“医学所要实现的远远不止征服、控制疾病,而是超越疾病以提升‘人的本质’,改变‘自然的’生物物理状态和心理健康状态”[9]115。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创立的医学研究公司Neuralink聘请了一些世界著名的神经科学专家,计划研发超高带宽脑机接口系统,来提高人类的记忆力和智力。公司的终极目标是通过技术从本质上“升级”人类,让人类可以与计算机设备实现思想互动,与人工智能“共生”。2018年2月,在迪拜召开的世界政府峰会上,马斯克在演讲中表示,我们只有变成“赛博格”,才不至于沦为无用的人。而要继续对经济有价值,“生物智能和机器智能的融合”必不可少[10]。
于是,医学的重心从以人为中心的医患沟通,转向一种人与技术的对话和互动。医生的职能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后人类影视作品中就展现出这种医学观的流变:医生形象不再是传统意义上“治病救人”的医生,而是对身体部件进行修理、组装或升级的“技师”。如2019年的漫画改编电影《阿丽塔:战斗天使》(Alita:Battle Angel)中,依德医生对自然身体受伤的病人的治疗方式就是帮助其组装可替代的义体和机械零件;而2017年的漫画改编电影《攻壳机动队》(Ghost in the Shell)中的欧莱特医生则在实验室中设计完美的赛博格身体,这样的身体可以与人类意识形成完美融合,以挑战人类的生理极限。
通过科技手段开发出完美的赛博格身体,从而拓展人类潜能,是自由人文主义在当代科技语境下的思想投射。超人类主义者认为,人类可以利用科技来超越当前的生存限制。高新医学技术可以消除残疾、疾病、痛苦、衰老甚至死亡等对人类生存和发展不利的因素。通过增强人类的智力、生理和心理能力,我们可以摆脱身体的限制和死亡的命运。马克斯·摩尔(Max More,又译马克斯·莫尔)在《超人类宣言》(Transhumanist Declaration)一文中说道:“成为后人类,就意味着超越‘人类状况’定义中的负面效应和局限。”[11]作为一种国际性的科技文化运动,超人类主义设想通过医疗技术来改良自然身体,实现一种“形态自由”(morphological freedom),并以超越、战胜死亡为其终极目标。在超人类主义者看来,现代科学虽然以认识、应用自然规律为基本方法论,其终极目的却是超越、战胜自然对人类的限制,而后人类将免受疾病、衰老和死亡的局限,拥有着更广阔的身体自由。
可见,超人类主义哲学融汇了自由人文主义的乐观进取精神和身体机械论的技术理念,将赛博格身体视为超验性意识的技术化延伸。人的价值在于不断对自我的极限进行超越,而超人类主义正是试图通过医学科技来实现人对自我的超越。人类向后人类的过渡被视为从童年进入成年,是人类进化中理所当然的下一步。
超人类主义技术设想肯定了后人类主义身体观,然而,这种思维模式依旧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之上,并未对其核心价值以及二元对立结构进行质疑和反思,而是想象出一个人类与技术融为一体的乌托邦未来。这种技术主义逻辑试图通过技术改进、净化人类身份,创造出更新、更强的人类物种,以扩大和增强人类功能,使之在未来技术语境下更高效地运作。就此而言,后人类并非人的终结,而是在当下技术话语中形成了“生命的去物质化和存在的意念化”,从而大大拓展了人类意识的领域[12]。21世纪以来层出不穷的银幕超级英雄形象就是超人类主义的流行文化产物,西方个人主义神话借助科幻想象得到了延续。超级英雄们通过医疗科技和机械装置增强身体能力,却仍然保持着传统意义上的价值理念。无论是靠药物对身体基因进行改造(如美国队长、蜘蛛侠),还是依靠机械设备对身体性能进行提升(如钢铁侠、蚁人),都体现出超人类主义视角下自然身体与技术的完美融合。
三、忒修斯之船:“技术人性”下的伦理困境
超人类主义提倡身体与技术的融合,在进步和理性的名义下通过医疗科学来超越脆弱肉身的局限,改进人类的智力和体力,从而实现消除疾病、延长寿命甚至战胜死亡的目的。实际上,这种对未来“技术智人”(techno-sapiens)潜能的热情,避开了一些本体论议题。超人类主义声称应当通过技术提升重塑“人的本质”,但却对这个人类思想史上的终极哲学追问避而不谈。在后人类语境下,人的本质到底是什么?经由技术改良后的赛博格人类必然要面对“技术人性”(techno-humanity)对传统价值伦理的冲击。而赛博格身体改造所催生的新身份又如何融入当下的社会环境中?
作为生命科学对象的身体,在现代科技的塑造、改进中,不断挑战着人类社会的传统伦理价值。就现实文化语境来说,体外受精、心脏移植这样的医学科技打破了人们对身体局限以及对自我和他者界限的假定。赛博格技术是生物有机体与机器形态的融合,那么,主体如何将人工化的机械/生物器官融入自己的身体和身份认同中?由于移植替换了受体的身体功能,身体的习性、功能和感知发生了变化。这必然会模糊自我与他者、肉身与机械、人与动物的边界,从而直接威胁到人作为存在主体的合法性。
后人类身体和身份的伦理思考可以追溯到一个古老的哲学迷思——“忒修斯之船”。公元1世纪时,希腊哲人普鲁塔克(Plutarchus)提出这样一个关于身份更替的问题:如果一艘船上的木头不断被更换,直到所有的木头都不是原来的木头,这艘船还是原来的船吗?这个哲学悖论也可以引申到对后人类身份的探讨中:如果肢体和器官不断被义肢代替,甚至大脑也被技术介入,那“人”还是人吗?如果像马斯克所言那样,只有变成“赛博格”,才不会沦为无用的“人”,那么赛博格人类到底如何定义?如果医学技术语境下的赛博格实现了人体与机械的完美结合,那么我们还可以理所当然地继续着以“人”为中心的价值体系吗?
正是基于对后人类技术人性的质疑和挑战,海勒在赛博格的语境下,试图重新看待“人”这一概念。她指出,后人类主体是异质性的混合体,其中囊括了各种科技、社会、政治元素,因此,后人类身份实际上是一种“信息的实体”(informational entity)[1]3,由各种异质成分构成,并不断塑造着新的身份边界。后人类身体叙事的核心是自然身体丧失所引发的焦虑感,因此,影视作品的赛博格叙事起到了一种文化实践和协商的作用,一方面,赛博格身体意象意味着传统文化疆界(自然/人工、人类/机器、技术/生命)的崩塌;另一方面,赛博格概念也有助于想象、探索出一种科技与人的生存状况互相对话之下的、“人类”概念的新的疆界,从而对本质主义的人性概念提出疑问。
在《攻壳机动队》中,被抹去记忆、置换义肢后的主人公米拉见到智能机器人时总会不自觉追问:自己的身份是否只是电子大脑和义体的结合,也许“自我”根本就不存在?虽然欧莱特医生后来回答她说,身体无法定义自身,意识和灵魂(ghost)才是身份塑造的关键,然而这无疑又回到了笛卡尔式的身心二元论逻辑。而如果记忆是可以模拟、移植的,灵魂又何处寻踪?同样的身份追问也出现在《银翼杀手2049》(Blade Runner 2049)中。未来社会批量生产出复制人为人类服务,为了给复制人创造一种情感参照,从而更好地控制他们,生产商将记忆移植到他们大脑中。复制人K在得知自己身份的疑点后,踏上寻找自己的身份/灵魂之路,最后他发现自己的记忆是真实的,虽然那并非自己的记忆。因此,一个终极的哲学追问出现了:衡量人性(人类身份)的标准到底是什么?这些后人类科幻作品通过展现身体对个体意识和身份的塑造作用,将“人类身份”论争引向了更为开放的“后人类身份”概念。海勒就认为,以生物基质形成的具身化(embodiment)是一种历史的偶然,而非生命的必然。意识虽然被视作人类身份和灵魂的标志,但这只不过是一种启蒙理性和人类中心主义的幻想,意识只是进化中的突变,一个偶发现象。身体存在和电脑模拟、机械装置和生物基质之间不存在本质区别[1]3-4。随着科技对人的身体和意识的干预不断加深,人类身份已经无法固守传统意义上的稳定内在结构,而日渐趋于一种流动的、游牧式的建构过程。
自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的《神经漫游者》(Neuromancer)开始,科幻作品中的后人类医学想象层出不穷,除义肢和器官移植之外,还包括身体植入芯片、大脑外部插口以达到人机互联、远程遥控。可以说,这种科幻潮流是西方个人主义神话在流行文化中的延伸。无论是自我用药进行个体生理管理,还是人机结合的交互式生物技术,无疑都会使人从脆弱的自然肉身中解放出来。然而这种新的医学身体话语必然会改变人类情感体验和认知习惯,从而挑战传统健康和身体观念,乃至颠覆既有的人文主义认知结构。在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哲学中,人类精神——“灵魂”赋予了人类主体性和道德能动性(moral agency),即依据道德判断进行自由抉择的能力。那么强化的赛博格身体是否会对人的道德能动性产生影响?如果如海勒所言,技术改造后的人的身份是一种信息化实体,由之产生的“技术能动性”(techno-human agency)就是一种异质成分的集合体,那么人的能动性是否已不再是自由意志的体现,而是技术的产物?这些疑问共同体现了“技术人性”造成的伦理失序。
对于此,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最早展开了文学想象。小说中,主人公弗兰肯斯坦通过生化实验创造出了生命,实现了无母创造生命的男性幻想。然而创造出的怪物虽然具有学习能力,但因似人却非人的畸形身体,被人们所恐惧、排斥,而无法融入社会,在仇恨驱使下,怪物杀害了弗兰肯斯坦一家,并随后自焚。在其后的小说、影视作品中,技术创造下失序的身体意象不时浮现,折射出赛博格身体想象中蕴含的伦理困境,以及人类身体被非人、亚人类或未知物种等文化他者侵染所引发的恐惧。
《机械战警》(Robocop)及2003年版的《绿巨人》(Hulk)等影片就展现出技术/医学改良后的身体失去控制从而引发的身份撕裂和伦理困境。在《机械战警》中,警察墨菲在执行公务时被暴徒打死。科学家将他的大脑与机械身体结合起来,创造出配备高科技武器的王牌特警。在未来的机器城市底特律,被剥夺记忆的墨菲扮演着惩恶扬善的救世主形象,以他强大的机械身体挽救着一个面临崩塌的社会。然而墨菲的赛博格身体却退化到婴儿状态,只能靠服食婴儿食品为生。片中也不时浮现出他的人性(记忆、亲情、仇恨、创伤)和机械身体之间的矛盾,将观众引向技术社会中的人性异化。《绿巨人》中,受到伽马射线强力辐射实验的布鲁斯·班纳在发怒下,就会唤醒体内的神奇力量,变成失去自主意识的绿巨人,从而诱发超强的破坏力。绿巨人被技术侵染的身体体现了“人”的纯洁性的丧失,他的混杂身份代表着终极的“后人类状况”(posthuman condition)——科技不再是随意被人类驾驭的工具,而是侵入人类身体和意识中,从而形成新的“技术—人类主体”(techno-human entity)。
四、对话、协商:银幕赛博格身份的流动
自1927年弗里兹·朗(Fritz Lang)的《大都会》(Metropolis)问世以来,在众多科幻影视作品中,赛博格身体想象都携带着鲜明的历史、文化色彩,而不同时代的想象也投射出社会对于技术、个人身份和主体性的态度变化。赛博格想象凝聚着现代社会对人机结合的矛盾态度:一方面,技术化的赛博格身体在允诺着完美智力和体力的同时,也意味着“人”的纯洁性受到侵蚀,西方人文传统中被奉若圭臬的自由人文主义价值面临崩溃;另一方面,赛博格蕴含的强大身体潜力也被视为对本质主义人文价值的延伸。这种人/机器的二元对立在赛博格叙事中创造出一种叙事张力,体现出不同的思潮围绕“技术人性”主题进行的交流与协商。
如前所论,银幕赛博格想象指向了后人类语境下人类的生存状况,并对本质主义的“人”的主体性概念提出疑问。哈拉维将身份视作身份与主体性建构的关键因素,她指出:“身体不是被生出来的,它们是被制造出来的。”[5]208人的身体不但是自然演化的结晶,也受到社会规训权力的作用。她认为,赛博格的身体可塑性也意味着其身份的流动性,因而挑战着基于生物学之上的本质主义人类构想。哈拉维在流动赛博格身份中看到了一种解放潜力,认为赛博格标志着后性属(post-gender)文化的到来,可以打破父权社会逻各斯中心的本质主义伦理偏见,从而摆脱男性气质、女性气质的性别设定。赛博格的出现并非意味着“人的终结”,而是使得人的主体性建构跳出了传统生命政治学中的性别、种族偏见[5]151-152。
《攻壳机动队》《阿丽塔:战斗天使》同样涉及了身体改造所引发的身份焦虑和伦理困境,而与男性超级英雄电影相比,两部影片都探讨了赛博格身体与女性身份的关系。正如哈拉维所言,赛博格身体的流动性挑战了本质主义性别构想。康奈尔(R.W.Connell)指出,在父权文化下,男性通过锻炼形成机器般有组织、强悍的身体,战斗的狂喜得到赞美。男性注重行动,女性注重外貌,女性利用其“外表”,男性利用其“在场”[13]。而银幕赛博格女性身体象征着“外表”与“在场”的结合,在二元对立的性别规范之间形成了对话与协商。一方面,赛博格女性跳脱了传统性别的定义,她们的银幕身体呈现一种对传统男性气质的操演,然而影片的女性身体奇观被赋予一种时尚化、暴力化的视觉表征,从而避开了更深入的对女性身份的探讨。这既是一种对女性的主体赋权,也是一种客体化运作。这种以男性凝视界定的理想化的女性气质实际上仍然铭刻着传统父权秩序下对女性性别身份的想象[14]。但另一方面,赛博格女性的身体奇观又在一种“技术化怪怖”(technological uncanny)中挑战着这种性别话语规训。在《攻壳机动队》最后的搏斗中,米拉强悍的赛博格躯体因用力过猛而崩裂,她体内的电线和机械零件倾泻开来。《阿丽塔:战斗天使》中也展现出主人公健硕的身体在搏斗中碎裂的恐怖意象。倾注着男性凝视的女性身体在毁灭意象中释放出一种瞬间的“反凝视”(counter-gaze),指向了银幕身体塑造中的性别权力机制。两部影片中,主人公最后都通过自身努力,在视觉奇观中摧毁对手,完成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和对技术身体的把控。
21世纪后涌现出的,由漫画改编而来的超级英雄电影(以下简称超英电影)代表了另一种自由人文主义与后人类议题的对话与协商。超英电影中大量涉及了基因改良、人机合体等医学实验对自然身体的塑造。其中也描述了技术介入所引发的身体失控和人格分裂,然而钢铁侠、美国队长、蜘蛛侠等中心人物在经由身体改良后,却仍然恪守着传统价值理念。超级英雄们的赛博格身体虽然展现出一种模糊和流动性,但影片叙事和视觉审美却都影射了传统的二元对立式的身份塑造。技术改造过的后人类身体被呈现为两种不同的视觉编码,即善良的、自然的、与技术融合的英雄们,对应邪恶的、人工化的、被技术污染的反派。超级英雄们代表了技术与生命完美融合而形成的新的科技主体,而反派身上却体现出对技术主体身份的焦虑。因此,超英电影的身体叙事试图用一种传统的本质主义框架来限制后人类思想的解放潜力。反面人物技术改良后失序的身体被妖魔化,而超级英雄们身上则体现出有序的、成功实现技术生物融合的“人”的身份。最终他们通过摧毁对手,展现出其身体优越性和男性气质。这种“更强的力量带来了更多责任”的超级英雄宣言,体现了一种保守主义的身份和身体政治——拒绝对技术主体性带来的身份撕裂和伦理困境进行反思,而是意图通过技术手段来延续并扩展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由此,超级英雄电影实践了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将纷繁复杂的后人类论争纳入泾渭分明的传统性别和种族身份表述中。在《钢铁侠》(Iron Man)系列中,身体经由技术改良后的“钢铁侠”托尼·斯塔克竟然因此变得更为人性化了:他从一个冷漠自私的军火贩子转变成了一个富有温情、责任感和牺牲精神的公民。
究其渊源,赛博格身体凝聚着两种对立的文化想象:“被侵染的”和“纯洁的”身体。如果说机械战警、绿巨人、米拉、阿丽塔的赛博格身体折射出“技术人性”带来的不安和矛盾情绪,钢铁侠、美国队长等超级英雄形象却是对技术身体改造的理想化投射。超级英雄们在进步的名义下,借助科技来超越自然生命的局限。钢铁侠的机械身体和心脏使他变得更人性化、更完整,他对于机械身体装备熟练的、近乎直觉化的运用,体现出自然身体和生命的完美的技术延伸,而反派对身体失败的、不自然的技术改造则显露出了其邪恶本质。另外,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超级英雄完美的技术化身体也传达着美式霸权所推行的尚武精神,而正是后人类科幻语境赋予了这种身体逻辑正义性。于是,超英电影的身体想象实际上避开了对技术人性的深入探讨,将后人类身份框定在本质主义的思想架构中。海勒将这种超人类主义逻辑与资本主义商品文化联系起来,认为这种离身化超人想象“是对后人类主义精神的去语境化和简化,这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最引人质疑的部分带进了新千年”[15]。如其所言,在流行影视展现出的超人类身体奇观中,身体在技术话语中被降格为物化的商品,反而使得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身体隐匿不见了。
五、结语
作为科幻文艺作品的核心母题之一,后人类身体叙事是对人类生命形态的终极哲学追问。身体作为主体性建构的关键因素,在后人类科幻电影中构成了一个话语交锋、协商的场域。事实上,后人类身体蕴含的矛盾性早在其创始作品《弗兰肯斯坦》中就已预示。作为对生命科学的原初想象,弗兰肯斯坦的怪物体现出自由人文主义者通过科技创造完美身体的愿望,而其失控的身体意象也警示着这种危险欲望的后果。
在当下社会,虽然科技话语不断冲击着传统身体和身份定义,自由人文主义思想传统所推崇的超验性的“人类精神”却借助技术想象在流行文化中重获生机。人们可以在与技术的融合中延续、拓展“自我”身份。在这个乌托邦化的科技未来想象中,人类与技术形成了一个新的主体,这个主体成了现代人的继任者。究其根本,超级英雄叙事的深入人心,正体现出科技资本崇尚的超人类主义思维在当下社会的甚嚣尘上。哈拉维等思想家在后人类身体想象中发现的文化解放意义,也日渐迷失于纷繁复杂的技术和消费话语中。正因如此,随着“后人类”观念从“遥远地平线的云彩”逐渐迫近现实,在后人类身体中发掘出一种新的身份建构逻辑,无疑有助于弥合人类社会内部的纷争。
通信作者:林伟,广州中医药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讲师,研究方向为英美小说研究、文化研究、电影研究。
参考文献
[1] 凯瑟琳·海勒 . 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 [M]. 刘宇清,译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2] JAMESON F. Progress Versus Utopia;or,Can We Imagine the Future?[J]. Science Fiction Studies,1982,(19)2:152.
[3] 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 [M]. 庞景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4] 林伟 . 无形之体:科幻虚拟女性的银幕具身化 [J]. 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23(5):1-4.
[5] HARAWAY D.Simians,Cyborg,and Women: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M]. London:Free Association Books,1991.
[6] FOUCAULT M. The Order of Things: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M]. London:Vintage,1994.
[7] BRAIDOTTI R. The Posthuman[M]. Cambridge:Polity Press,2013.
[8] 黛博拉·乐普顿 . 医学的文化研究:疾病与身体 [M]. 苏静静,译 . 北京: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2016.
[9] 余泽梅 . 赛博朋克科幻文化研究 [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20.
[10] 马斯克宣布,脑机接口公司将在下月重磅更新,赛博格将成为现实?[EB /OL]. (2020-07-16) [2023-06-12]. https://user.guancha.cn/ main/content?id=348494.
[11] The Transhumanist Declaration[EB/OL].(2019-07-30)[2023-06-12]. https://www.humanityplus.org/the-transhumanist-declaration.
[12] HASSAN I. Prometheus as Performer:Toward a Posthumanist Culture?[J]. Georgia Review,1977,(31)4:835.
[13] 阿雷恩·鲍德温,布莱恩·朗赫斯特,斯考特·麦克拉肯,等 . 文化研究导论(修订版)[M]. 陶东风,和磊,王瑾,等,译 .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14] 林伟 . 女性奇观、银幕经济与女性凝视——劳拉·穆尔维《后影像》中的观看机制探究 [J].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23(3): 105-112.
[15] HAYLES N K. Wrestling with Transhumanism[EB/OL].(2011-09-01) [2023-06-12]. https://www.metanexus.net/h-wrestling-transhuman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