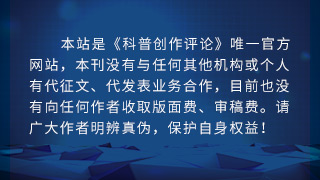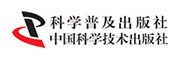自然博物实践与创作:从爱好者开始
科普创作评论
张海华
2026-01-16 14:01
到2025年,我开展自然博物观察与记录,从事自然生态题材的报道与科普文学创作,已经整整20年了。这20年,也正是中国民间自然博物实践与创作发展最快的20年。非常有幸,作为一个民间自然爱好者,我个人的自然博物实践历程刚好与时代发展“完美同步”。这看似巧合,其实也是必然。本文拟结合本人的自然观察、阅读与写作的粗浅经验,谈谈自己在博物类作品创作方面的一点心得与体会。
一、“大山雀”,一个报道大自然的记者
最近20多年间,国内博物爱好者、自然摄影爱好者群体迅速壮大,特别是从2010年以后,发展势头尤其迅猛。以鸟类摄影爱好者为例,2000年前后,整个浙江喜欢拍鸟的人屈指可数;2005年之后,浙江的鸟友数量开始明显增加。不仅浙江如此,国内很多地方的观鸟、拍鸟活动都逐渐蔚然成风。2007年春末,中国鸟类摄影年会在浙江省衢州市开化县的古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举行,吸引了很多来自国内各地的鸟类摄影爱好者。
如今,国内鸟友的数量已多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甚至,当某地出现一种罕见鸟类时,会有很多鸟友迅速坐飞机前去拍摄,动不动就出现“大炮”(超长焦镜头)云集的“名场面”。与此同步,近些年来,国内的昆虫爱好者、植物爱好者等各类自然爱好者的数量也在骤增。
而我本人的博物之旅,也正是从拍鸟起步的。可以说,目前在宁波,我的网名(同时也是“自然名”)“大山雀”远比我的本名张海华知晓度更高。我是一个自然摄影师兼自然科普作家,迄今已出版11本专著,涉及鸟类、两栖爬行动物、野花等。不过。在读大学时,我的专业背景分别是哲学和中国古典美学,职业则是记者与编辑,但这些与自然博物相关学科毫无关系。喜欢自然摄影与博物观察完全属于业余爱好,而且有这么一个爱好,也是纯粹出于偶然。
2005年2月,在一次采访途中,我在宁波城郊的农田里偶遇成千上万的麻雀,于是忘了正事,跳入田中认真拍麻雀。这原本是无意的一拍,谁知此后竟一发不可收,狂热地爱上了观察、拍摄野生鸟类。
现在回想起来,喜欢上观鸟、拍鸟,乃至之后痴迷于各种门类的自然探索,都跟我童年时代未被满足的好奇心有关。我自幼在江南水乡长大,对鸟儿、青蛙、野花等都非常好奇,可是很无奈,写作文时总要写“不知名的小鸟”“不知名的野花”之类,没人能告诉我它们的名字。到了30多岁,我终于有条件自己寻找、发现身边的野生动植物,并想办法知道它们的名字,也算是某种“格物致知”,这真的是非常有成就感也非常快乐的事。
开始拍鸟的六七年后,宁波有分布的绝大多数鸟类我基本都拍到了。于是,我决定选择新的领域进行探索。那时候,由于工作太忙,我常常只有周末晚上才比较自由。因为白天缺时间,我便打算去夜探本地的两栖爬行动物,那些动物基本都是夜间活动的。
不过,夜探自然并不容易。在2012年夏天我刚开始寻找、拍摄宁波蛙类时,根本找不到一本合适的专业图鉴。要知道,国内第一本全面介绍中国两栖动物的巨著《中国两栖动物及其分布彩色图鉴》(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到了2012年12月才出版,而且我也在比较晚的时候才得知并购买此书。起初,我能找到的关于本地蛙类的唯一资料是宁波市林业局的一份关于野生动物资源的调查报告,该报告列出的宁波的蛙类只有十六七种。另外,尽管2010年之后国内观鸟爱好者已非常多,但与之相比,至少在当时,我几乎找不到夜探自然的同好者——这就少了很多互相交流、共同提高的机会。
于是,在背景知识几乎一片空白的情况下,我决定采用“笨办法”,即从自己熟悉的溪流开始,逐条去探索,相信一定可以弄个究竟。我购置了头灯、高亮手电、闪光灯,开始夜间深山溯溪之旅。花了多年时间,宁波有分布的两栖动物我终于基本都拍到了,并且证实宁波的蛙类(含蟾蜍)肯定超过25种。那个阶段,我戏称自己变成了“蛙人”。
2014年,我又开始关注宁波的野花,十年如一日,乐此不疲地进山寻觅各种乡土野花,可谓“花痴”一名。目前,宁波多数有较高观赏价值的野花我也都拍到了。
可能有的人认为,拍花要比拍动物容易一些,毕竟植物是生长在那里,不会移动。其实不然。某些珍稀植物原本就非常难找,而要拍到它们的花更是不容易。比如说,受气候影响,植物的花期常有变化,或提前,或推迟,都很正常。有时,千辛万苦进入深山,找到了那种心心念念已久的植物,却发现它的花快要开败了,心里就会十分遗憾,因为这意味着“错过等一年”。而如果真如花友们所说的“花开得正好,我来得正巧”,那就别提有多高兴了。
近些年,我还在有计划地调查、拍摄宁波的昆虫,变成了一个“虫迷”。就这样,最近十几年间,我从一个“书生气十足”的人,变成了一个涉猎鸟、蛙、花、虫等多领域的“博物玩家”,一个报道大自然的“专业”记者。
二、见证博物爱好者群体的融合趋势
在某种意义上,我个人的“博物历程”,也是最近20多年来国内博物爱好者群体发展的一个缩影。而且,当这个民间群体达到一定的规模之后,一个普通的爱好者也完全可能在某种机缘下变为“公民科学家”,为专业的科研领域作出贡献,这在全球范围内都有不少先例。
就我个人而言,曾发现过多种属于浙江分布新记录的鸟类,也曾发现过多种属于宁波分布新记录的蜻蜓,这些都为当地的生物多样性调查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特别令我自豪的是,我还拍到了一种此前未被描述、发表过的新种角蟾——后来被中山大学的科研团队命名为道济角蟾(Boulenophrys daoji)。
其实,能有这份贡献,说稀奇也不稀奇,因为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很简单,职业科学家毕竟是少数,而当业余自然爱好者的群体数量与认知水平都明显提高的时候,就相当于多了无数双凭着热爱在日夜观察大自然的眼睛,这当然能为科研提供不少助力。
那么,为什么近些年国内的博物爱好者群体壮大得如此之快?今后又会出现什么样的趋势?
先来探讨群体壮大的原因。这一方面是随着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的提高,人们有了更多的休闲时间,也有了更多的兴趣去探索自然;另一方面,也跟数字摄影、互联网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密不可分。
进入新世纪之后,数码相机逐步在人群中推广,使得拍摄野生动植物的成本大幅下降。拿拍鸟来说,如果用胶卷来拍摄,那么其后期成本是绝大多数人无法承受的;随着“按快门不费钱”且性能强劲的数码单反相机(目前已被数码无反相机所取代)的普及,连拍摄飞鸟也变得日益简单。
而近些年,随着智能手机的崛起,普通人不但可以用手机随手拍身边的动植物,还可以用相关软件“扫一扫”,或者上传照片、录音,快速识别出具体种类。虽说这种识别有时并不准确,但多数情况下可以提供大致可靠的参考答案。这意味着,如果只是需要知道一个陌生物种叫什么名字,那么这件事正变得越来越容易。
基于以上因素,显然,对于当代的广大博物爱好者来说,初步认知自然的门槛在逐步降低,野外探索的效率随之提高,这有利于打破不同类型自然爱好者之间的“专业壁垒”。
进一步说,“分门别类”这件事,本来就是人类为了研究这个世界而发明的“方便法门”,大自然本身就是万物互联、彼此共生的。举个简单的例子,很多蝴蝶出现的地方与时节,总是与特定的寄主植物、蜜源植物密切相关,因此要了解某种蝴蝶的生活史,必然要大致了解相关植物。
因此,当资深博物爱好者开始不满足原有的单一门类的爱好,而开始涉猎其他门类时,大家必然会更多地互相“串门”交流。事实上,目前这已经成为一个明显的趋势。更何况,如今社交媒体的发达也在客观上促进了这种“串门”交流,使得大家在“跨界”领域得到更快的提高。
是的,我敢说,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更多的自然爱好者将变得越来越“博物”,而不再像以前那样只是单纯观鸟,或拍花、拍虫。这里,还是拿观鸟(含拍鸟)爱好者来举例。观鸟这项活动在国内起步算是比较早,目前在中国的自然爱好者群体中,“鸟人”的占比很大,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资深“鸟人”在喜欢鸟类的同时,也开始转向别的博物探索之路,如进入野花、昆虫、哺乳动物、两栖爬行动物等领域;反之亦然,不少早年喜欢植物的人也开始学着观鸟,或关注其他领域。比如,我的好朋友、宁波知名植物达人小山老师(胡冬平先生),原先一直在探索植物,而近几年他也开始关注身边的鸟类、昆虫,并且兴味盎然。于是,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会不时向小山老师请教有关野花的问题,而他也常会发照片给我,问那是什么鸟或什么虫。
我也相信,一个喜欢博物的人更容易由“格物致知”做到“触类旁通”,慢慢地就会“师法自然”。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当代中国博物学倡导者刘华杰老师曾说:“浮生常博物,记得去看花。”这句话十分有名,常被广大自然爱好者引用。我想,这句话中的“看花”实际上体现了一种爱自然、爱博物的人生态度,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人生观、一种存在方式。
三、探索博物创作选题的三个层面
我是一名记者,职业决定了我在自然探索的过程中必然也会进行大量的相关报道。这些与自然科普密切相关的报道既包括即时的新闻,也包括时效性不那么强的副刊作品。后来,在宁波出版社领导的建议下,我开始有计划地写书。这些书属于科普作品,同时注重趣味性与故事性,文字本身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因此也可以说是自然文学作品。因此,我出版的大部分书,都深受中小学生喜欢。
近些年,在国内出版界,博物类图书的出版可谓掀起了一个热潮,既有大量从国外引进的优质书籍,也有不少国内原创图书。这里,我想围绕博物科普、自然文学原创作品的创作这一话题,结合个人粗浅经验,谈一谈自己的想法。
根据个人创作与阅读经验,我认为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进行博物创作,即自然图鉴创作、乡土博物与自然文学创作、博物跨界类创作。这三个层面本身没有高下之分,只要能做到深入浅出、内容生动、读者爱看,就非常有价值。
(一)自然图鉴创作
出于辨识物种、扩大知识面的刚性需求,我买了大量野生动植物图鉴,从轻薄便携的“口袋本”,到超大部头的专业巨著,都有不少。
首先,从具体内容来说,这些图鉴大致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以某地的特定物种为对象出版的图鉴,比如说某地鸟类图鉴或某地观花手册,或某物种的野外识别手册等,这一类出版物占了国内博物图鉴类书籍的绝大部分。第二类是以一个特定地区的常见(特色)物种为对象,进行综合性介绍的图鉴,如某地自然观察手册或某地自然笔记之类。
其次,若从图鉴的读者对象来说,也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主要面向专业人员的,其内容也好,行文也好,都特别注重科学、严谨、规范;二是主要面向普通爱好者的,内容通常要简略一些。当然,这两者并无绝对的界限。
这里针对那些面向普通自然爱好者的图鉴,发表一点个人浅见。我觉得,国内近些年出版的博物图鉴类书籍数量虽多,但真正的精品不多。很多图鉴,是以图片加简单文字介绍的方式来呈现,而且这些文字介绍多以专业词汇出现,不接地气,初学者看了之后往往不得要领,没有阅读的乐趣,久之甚至可能生厌。所以,我很希望,今后能见到更多实用、美观,同时也非常鲜活、有趣的图鉴类作品。这些图鉴作品,在讲究科学严谨的同时,也能有更多的个性化表达,比如说多介绍一些作者在进行实际博物观察时的心得(可以是成功经验,也可以是失败教训),相信一定会对读者大有裨益。
(二)乡土博物与自然文学创作
与图鉴类作品主要强调科学性、实用性不同,乡土博物与自然文学作品不仅介绍乡土物种与环境,同时具有“自然探索笔记”的性质,因此在保证科学性的基础上,同时要求具备较强的文学性。
博物学是一门特别讲究“在地性”的学问。20年来,我关于自然博物实践的理念一直是“乡土优先”。在具体创作方法方面,我近些年也做了一些探索。
2017年秋天,我的第一本书《云中的风铃:宁波野鸟传奇》由宁波出版社出版。这是宁波第一部关于本地鸟类的科普著作,也是一部自然文学作品。它以散文形式讲述鸟儿的故事,还有“鸟人”趣事,以及鸟与古诗的故事。全书约500张彩图,生动展现了60多个科的300多种鸟儿。
写这本书之前,我花了很长时间来思考如何把这本科普读物写得生动有趣。比如,文中会涉及大量的对鸟类外貌、习性的直接描述,这些描述如果按照科学图鉴的语言来陈述,虽然看上去准确性没问题,但难免会显得比较枯燥,普通读者不爱看。在我为此头疼的时候,刚好读到了欧仁· 朗贝尔(Engène Rambert)与保罗· 罗贝尔(Paul Robert) 合作的《飞鸟记》(Les Oiseauxdans la Nature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此书已有100多年历史,其中对鸟类特性有趣、俏皮的描写让我茅塞顿开。在写《云中的风铃:宁波野鸟传奇》(宁波出版社2017年版)时,我借鉴了《飞鸟记》的对鸟类的写法,同时结合自己寻鸟、拍鸟的鲜活故事,注重细节,注重情感,力图把自己对鸟类的热爱通过文字传递给读者。2018年秋天,《云中的风铃:宁波野鸟传奇》荣获“首届中国自然好书奖”,以及浙江省关于出版物评奖的官方最高奖——第27届浙江树人出版奖·图书类正式奖。
后来,重点介绍宁波两栖爬行动物的《夜遇记》(宁波出版社2018年版)、介绍宁波野花的《野花有约:宁波四季赏花之旅》(宁波出版社2023年版)也陆续出版。
与此同时,我还依靠多年来掌握的关于宁波野生动植物的知识,通过对本地特定区域的野外本底调查,撰写以体现生物多样性为主题的图书,如《东钱湖自然笔记》(宁波出版社2020年版)、《龙观自然漫步》(宁波出版社2022年版)、《棘螈和它的朋友们》(宁波出版社2025年版)等。
近些年,在写书的时候,有两位老师的著作对我影响很大,他们分别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刘华杰先生和著名诗人、博物作家李元胜先生。非常荣幸的是,几年前,我和两位老师一起,受西双版纳勐海县委宣传部委托,创作“勐海五书”中的3部,分别涉及昆虫、植物和鸟类,均需在野外调查的前提下进行写作。李元胜老师的《勐海寻虫记》(重庆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率先出版,刘华杰老师的《勐海植物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继之。两位老师均采用第一人称叙述各自的考察经历,虽文风不同,但各有其美:李元胜老师的文字情感饱满,叙述生动,很多地方充满诗意;刘华杰老师的书内容翔实严谨,多有独到见解,学术气息相对较浓,但依旧能做到娓娓道来,令读者难以释卷。我的《勐海观鸟笔记》(重庆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在写作时,也尽量向两位老师学习。
无论是自己写书,还是读别人的书,在博物创作领域,比较难的一点是如何做到把内容的科学严谨与叙述的生动有趣较好地结合起来。对此,我的个人经验是,尽量用第一人称视角来写,这样既可以充分体现自己在自然探索过程中的故事细节,也有利于适度地表达感情,使得文章富有感染力。同时,我的写作通常以讲故事为主,在注重可读性的基础上,很自然地穿插各种科普内容。
有一种观点是,科普文章不宜有明显的感情色彩。在我看来,博物活动本身就是一项颇有个性化的活动,注重观察者、参与者的主观感受,因此适当多一点感情色彩也是无可非议的。作者要把握的,是不要让这种情感的“浓度”越过“科学严谨”的边界。
(三)博物跨界类创作
与自然图鉴、乡土博物与自然文学类这两大类作品相比,博物跨界类作品存在突出的“原创佳作”短缺问题,虽然国内出版数量不少,但同质化较多。
比如说,关于《诗经》的博物解读类出版物近些年就有不少。出于写作《诗经飞鸟》(宁波出版社2020年版)的需要,我购买了大量相关书籍。个人最喜欢的是,我国台湾的潘富俊所著的《诗经植物图鉴》(猫头鹰出版社2014年版),作者为此书的写作下了很大功夫,整本书内容翔实,排版精美,令人赏心悦目。但这类书的问题也非常突出,2015年以来,细井徇(Hosoi Jun)的《诗经名物图解》(『詩経名物図解』)①在国内突然红了起来,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中国画报出版社等超过10家出版社为其配以相关译注,重新编排、制作后出版,有些还做成了少儿版,但内容基本大同小异,且不属于当下原创。
关于二十四节气的博物、文化解读,情况也类似。这是近些年的一大出版热点,但佳作并不多。在准备以“二十四节气里的宁波物候”为主题开展写作时,特意买了不少相关书籍。直到最近,读到“气象先生”宋英杰所著的《二十四节气百科全书》(中信出版集团2025年版),才觉得找到了一本真正扎实可靠且能体现最新研究成果的参考书。
这两年,我读到的另外一本博物跨界类佳作,当属《形理两全:宋画中的鸟类》(浙江古籍出版社2024年版)。此书作者是曾任浙江省博物馆馆长的鸟类学家陈水华。陈水华对174幅宋画作品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可辨识到具体鸟类物种的画作数量占比高达88%,其中可辨识鸟类共计67种。他据此写了一本非常有趣的书,全面介绍宋画中的鸟类,在古代绘画与现代观鸟之间搭起一座跨界的桥梁。
我本人也历时近5年,完成了《诗经飞鸟》。2016年春天,我准备写一篇关于“古诗中的鸟儿”的文章,发到报纸专栏上。写这一题材,《诗经》肯定是绕不开的。做功课翻阅《诗经》时,才发现提到了那么多种鸟,光就《诗经》便可以单独成文了!再仔细读下去,发觉又不对,原来只针对“关关雎鸠”就足以写一篇有趣的文字了!于是,不久之后,《雎鸠是个什么鸟》发表在了《宁波晚报》副刊上,颇受读者好评。
受到鼓舞后,我索性一鼓作气,用了几个月时间,基本梳理出了《诗经》中提到的所有鸟类,并陆陆续续又发表了几篇文章,形成了“《诗经》鸟类漫谈系列”,总计一万多字。那个时候,我就思忖着是否该写一本书了。但这一来,工程就大了。于是,又花了3年半的时间,用来读书、写作及野外拍摄,才完成了书的初稿。此后,又经过近一年的调整、设计、制作,这本书才得以面世。
在此书的“自序”中,我说:“我写这本书,其目的,并不是想写一本像博士论文一样的‘专业’学术著作,而是希望自己能尽量以生动、简洁的语言讲清楚诗中的鸟,并适当穿插一些自己亲身经历的野外观鸟故事,从而能让高中生(甚至文学功底较好的初中生)可以不太费力地读下去。同时,为了让书的阅读界面更加友好,除了尽可能备齐相关鸟类照片,我还让女儿用水彩手绘了不少相关鸟类,用作书中的插图。就题材而言,本书是一部跨界作品;同时,我希望它的作用,也是能够在博物学与古典诗歌之间架起一座小桥,让更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爱上自然,爱上《诗经》。如果能这样,该是多么美好的事!”
四、期待博物创作的未来更加多姿多彩近些年,国内在博物学发展方面一直热度不减,这里不说专业领域的研究,单就民间爱好者的层面而言,喜欢自然观察与摄影的人越来越多,喜欢带孩子参加自然探索活动的家长也越来越多,这显然是件大好事。
不过,在博物创作领域,我觉得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下面简单谈谈涉及四方面的一点浅见。
第一,虽然当下博物出版物数量众多,但从国内博物类作品评奖结果来看,获奖的优秀作品多为国外引进版的图书,国内原创类作品相对较少。这需要国内作者与出版社共同努力,在保证数量的基础上进一步打磨质量,争取出版更多从内容到形式均具一流水准的原创精品。
第二,博物跨界类原创佳作相对比较稀缺。其实,中国的古典文化本身就具有“不隔自然”的传统,特别是在文学、绘画等领域,更是蕴含着海量的博物“富矿”,值得我们去挖掘,去发扬光大。民间博物爱好者来自各行各业,完全可以结合自己的专业,对博物学进行各自的解读,假以时日,相信一定会大放光彩。
第三,目前国内喜欢自然摄影的人群庞大,与之相比,专长于博物手绘的人却非常少。其实,在博物领域,手绘具有照片不可替代的巨大优势。比如说,照片限于光线、角度、拍摄者的主观选择等因素,有时并不能反映某个物种的关键特征,而科学手绘作品更容易做到这一点。此外,手绘作品很多时候比照片显得更有人文温度,更具审美价值。希望今后能有更多的有心人能学习、精通博物手绘,这样的话,我们的博物创作一定会如虎添翼,更加多姿多彩!
第四,要重视自然录音,抢救和保护“大自然声景”(声景,即soundscape,或译为“声境”),并应用到博物创作中去。目前,国内喜欢自然摄影摄像的人越来越多,而专心做自然录音的人寥寥无几,相关人才极为稀缺。我相信,大自然的声音,不仅可以让人在疲累之余沉浸其中,起到疗愈心灵的作用,也可以唤起保护原生态之心,保护一方可以享受天籁的美丽、安宁的土地。如果应用到博物创作上,也一定可以别开生面。
①处于日本江户时代的儒学家细井徇,曾组织京都画师,共同编撰绘制了《诗经名物图解》,涉及《诗经》名物200多种。此书采用彩色绘图,画面唯美,质感细腻,比冈元凤(Oka Genpou)的《毛诗品物图考》(『毛詩品物図攷』)精美不少。
*通信作者:张海华,宁波晚报社记者,自然摄影师、博物作家,主要从事宁波本地生物多样性调查、拍摄与写作,兼及“古诗里的博物学”研究。705335325@qq.com。